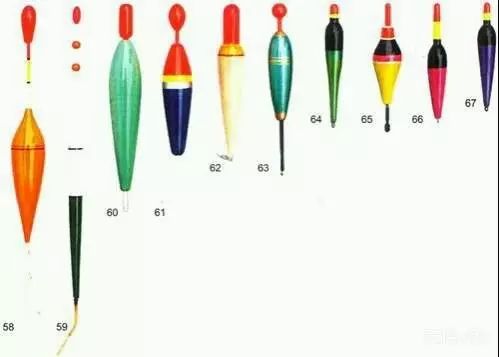想着写鱼的刹那,鱼的故事便如过江之鲫朝我涌来——
我的时间凝固在那一瞬,只听见鱼游走的声音。我的世界只剩下了水,以及虚幻的水中鱼的俯冲或闪躲。
我避不开鱼对我的冲击。稍微闭一闭眼,那些咬穿鱼钩痛苦不堪的鱼,那些石灰水中气如游丝的鱼,那些随着炸药的轰隆惊叫在水面的鱼,那些带电奔逃仓皇失措的鱼,它们,在此刻,咬住了我的神经,我便仿若一条垂死的鱼,我知道,我的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等待我的,当然还有严厉的拷问。鱼,在那儿,它们的眼从未闭过。

我的疼痛,终于在这样一个伤感的故事中停顿下来:
深秋一个浓雾紧锁的清早,我朋友的弟弟随他的伯父跌跌撞撞到了早就喂好窝子的水边,那天,它们兴奋中期待着全新的收获,就像老农自信地走向金灿灿的麦浪。那真是一个十拿九稳的幸福时刻,作为经验丰富的伯父,没有任何插曲会惊扰他的计划,对这个藏鱼的地点,他已经调查了好久在心里琢磨了好久,何况还提前做好了无懈可击的准备。那么,就开始吧,一切都是有条不紊。伯父叫侄儿提好装满炸药的瓶子,然后蹑手蹑脚收拾电线远离河岸,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缺,就等那一声巨响,然后是白花花的一大片鱼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然后伯父和侄儿在掀翻的河流中抢收胜利的果实。
但是——,我不能不停下来,正如你可能想到的那样,侄儿没有听清伯父从浓雾里传来的含混的口令,装满炸药的玻璃瓶,在侄儿的手中爆炸了。
那是一个本不应该为一个少年生命的鲜血点染的秋天的早晨。太阳还没有出现,而一个13岁孩子的右手,作为对一次炸鱼的警示,断裂,纷飞,而后消散,从此与这位懵懂少年没有任何关联。
这个故事当然没有结束,就像炸鱼这种行为不因一个少年一只手的永远失去便戛然而止。
那个秋晨,连同那一声惊心动魄的爆炸,肯定已经留在了一些人的记忆里。
然而,当那条小河再次迎来她悄声细语,清且涟兮的时节,我们还会不会忆起那场惊悸?
欣赏春天,我们不会忽视一条细小的河流。她堤上的嫩柳,柳梢的烟霭;她岸边的青草,草尖的玉露;她水面的柔波,波上的春光。甚至她水流里悠游自在的小鱼,清晰可数的碎石。哦,一条小河,她流淌的喧哗的朗诵的,又岂止是水?

鱼,仿佛也是春天的使者,一时间倾巢而出,一条河昂昂然一片生机。
这样的时候,我的两位姑父会时常来到我家,同我的父亲兴致盎然一道垂钓。
河流穿过村庄,蜿蜿蜒蜒,随处可见的灌木丛、刺槐杨柳便是天然的标志,远远一望,就清楚河的大致走向。姑父们也不陌生,带上我们几个小屁孩,嚷嚷着就到了河边,随便一蹲,就是个垂钓的好位置。
等到祖母颠着小脚来喊吃饭的时候,我们抬着的鱼篓里已经蹦跳着不少的鲫鱼、鱿鱼、赤尾鱼之类。
那注定有一顿丰盛的晚餐,鲜鱼汤、糟辣鱼、芡粉鸡蛋鱼混炸,母亲和祖母忙前忙后,弄妥当的鱼抬上来,喷香的酒打开来,两位妇女露出少有的对笑,站立桌边,搓着手大声劝着大伙趁热吃。窗外的树在使着性子的绿,鸟在叽叽喳喳的飞,村庄祥和安静。
记得我的老家已经拆除的老木房里曾经有一柄锈迹斑斑的钢叉,长年闲置在一间不常进的老屋里,钢叉装在一棵长长的竹竿上,问母亲,母亲不语,问得多了,终于吐出一句:捉鱼用的。
我便纳闷了,五指般的钢叉,齿间距那么大,怎么抓鱼?问父亲,父亲感叹道:你祖上用的,听说那时这门口河里的鱼特多,肥大。站在岸上,盯准了鱼,一叉下去,就是一条。
我的眼前便打开一幅这样的图画:清代的某一个早晨或黄昏,我的祖父大步流星,草鞋踩响田埂的虫鸣,他把早已褪色的长衫的前襟捞起来掖进腰间的布带里,扛了那柄钢叉,握柄的手紧握一种自信,彷如一身的孔武。他这是要到哪里去?远远望开是那条流淌千年的河流,曲折在古老的田野。半袋烟的功夫,祖父的钢叉上已经悬挂着两条肥美的鲢鱼,而村口,是祖母隐隐约约走来走去的身影。

父亲摆古的时候,总会自豪地感慨:我们这儿曾经是鱼米之乡,那水宽阔平展,住在河两岸的男人们都有一手捉鱼的好功夫。父亲有点文化,父亲的语言便有了一丝丝的文雅。他的描绘总会出现并不雕琢的诗意。
我从小便有了大把同鱼往来的日子,那条河常常把我的惊叫与失落一点不少地拿进去,就像把所有无家可归的鱼拿进去。我们常常为一束浪花欢呼,也常常举着牛鞭抽打着滔滔的流水。
一年四季,看似年复一年不动声色的河流总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亦或困顿。有一次,我竟然钓出一个团鱼,在同伴惊羡的目光里,我家的小院彷如祥光普降,一片欢腾。而这时,祖母不合时宜地出现了,只见她小小心心捧起不大的团鱼,回头就给张皇中的小孩一阵的吼叫,那意思是说,钓了团鱼是要马上放生的,不能带回家,祖训不能不信,何况鱼儿还这么的小。

眼看一个院子的欢乐瞬间变成了泄了气的皮球,我很是大叫大闹了一阵,看看拗不过愤愤然的老祖母,也只好作罢。一帮小家伙便随了祖母来到河边,把团鱼庄重地放回河水。祖母双手合十,似在对鱼祈祷,也在替我忏悔。
夏夜的河边是很有些意思的,我们可以去钓夜鱼,一种名为刺疙疤的野鱼,傻却贪,它们出没的时间尽在晚上,白天它们躲在石缝里,仿佛在为夜间的觅食养精蓄锐。而夏夜凉爽神秘的河边,我们这群杀手悄然逼近。
极其普通的鱼饵,鱼线上一个依稀的标志,松软的草岸,随便一处扎下来。整个过程好似在彼此兑现一个承诺,鱼不断被钓起来,彷如探囊取物。个大的星星在深蓝的夜空悬着,在不知深浅的水底亮着,满河流的璀璨。
仿佛就在那一夜垂钓之后,老家离我远了,河流也不在内心淌响。我已经远离家乡在外谋生。
偶然回了一趟老家,那条我儿时不离不弃的河流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病怏怏了无生气,曾经扎猛子摸鱼的地方,曾经不钓鱼儿钓星辉的地方,曾经和小小的妹妹玩家家的地方,飘卷着白色的垃圾,水在怪异的石缝挤出一绺绺的细丝,也不是我儿时可以捧出就喝的干净。
鱼,在我们的酒桌时常出没的鱼,据说已经很难见到野生,那么几乎都是家养,宛如眼底许多事件中的矫情。

我便真正怀念起我的童年,羡慕起我祖父母的生活情调来。
曾经的小伙伴们告诉我,乡下已经多年听不见炸鱼的声音、闹鱼的事情,至于电打,也只是说归说做归做。
我哑然,我不明白,这是我们生活的悲哀,还是我们生存的幸事。
鱼,以及它们的故事鱼贯而入。我躲得远远的,我携着空落落的心,走在苍茫的河岸,走在一个人的河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