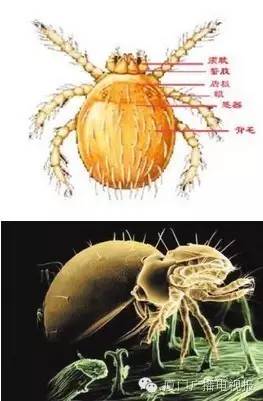一种梦境
郑峰
田园,黄昏,一直是我的一个梦境。
在故乡山村的孩童时候,就喜欢那浓浓乡野田园的黄昏景致。
我的村坐落在蓼花河畔南面,一个隆起的山丘地带上。三面又有起伏如涛似浪的青石山围绕着,每遇深色黄昏,正像鲁迅笔下的故乡的山势:黛青色,象铁兽的脊梁。
在围合的铁兽的西面,唯独网开一面,地势平坦,仿佛是上苍打开的一个通口,一直推向遥远的西天。这倒成了少年的我看日落黄昏的绝好天然条件。
后来,走出了大山故土,为工作、谋生和理想疲于奔波,跋涉江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失败与成功,沮丧与喜悦。《史记·汲郑列传》中所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时至今岁,人生百味尽尝大半。但不时,总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节,石光电火般地闪现一下儿时的黄昏一刹,那样快捷而轻盈,像是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描写的那青石潭中的百许头小鱼儿:“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来往翕忽,俶而远逝,似与游者相乐。”
这样的感觉和幻念,也时常出现在我的散文、小说和书画作品中。这也许身体基因中那个“黄昏、田园”情节吧。我想这样的情景和感受,恐怕不少朋友都有过吧。
此时,我坐在居室宽大的南窗口书桌的东头,面对窗外夏日特有的浓郁苍翠的树丛,又看到了那美丽动人的黄昏。只不过,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个退休闲居的老叟,那黄昏里,多了些许淡淡的落寞、忧伤和苍清,更多的是,如丝似缕的念想和思绪。
案头正有《中国书画报》展开,扑入眼帘的是南宋李嵩作的《赤壁图》:暗礁石壁,以小斧劈皴画之。寓拙重、沉凝于简括、遒劲之中;漩流急浪,用锯齿描精绘细写而成,于装饰美感中见激扬之势。远水无波、淡墨晕染,其景幽远;孤舟泛波、名士闲坐,抒怀古之情。
此景此图,堪为一伴,可书、可诗、可画,真乃田园黄昏图也!
也说读书改变命运
张鸣
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很实在的命题。上大学和没上大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绝对是一个分水岭,无论知青也罢,非知青也罢,上了大学,以后的路大抵比较平顺,进入体制,或者走出体制,一般都能混出个名堂。而没上大学的人,大抵就是继续做农民。进了城,也不久就下岗,生活相对困窘。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可能没上大学,靠倒腾生意发了财。
但是,在当今之世,这样的分水岭已经不存在了。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子弟,即使上了大学,也依旧摆脱不了困窘的命运。即使名校的研究生毕业,也有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很多二本、三本的大学毕业生,即使进城也只能做“蚁族”。
越来越固化的社会,社会的层级从中小学教育就已经开始了。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乡村,或者城里比较差的学校,培养出的学生考试能力相对就弱。尽管大学扩招,上大学不难,但这样差一点的学校出来的学生,只能上差一点的大学,毕业之后的前景,在入学时就已经确定了。相对好一点的单位招聘,如果本科是非211大学,问都不问。即使后来人家经过奋斗,上了好学校的硕士和博士,照样没用。
其实,读书改变命运这话,应该是指读书改变人。通过读书,人变了,改变之后的人,未必就一定会飞黄腾达,取得成功。有的时候,恰恰相反,在人被读书改变之后,反而有可能变得不那么具有功利性,对成功的热衷会大幅度降低。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渴望被读书改变。这样的改变,主要是读书可以让人们打开眼界、开阔视野、增加内涵。一个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不同,很大程度体现在气质上、人生的态度上。当然,这样的改变,跟人在物质上的成功,没有正相关。
可惜,现在的我们只会说读书或者知识改变命运,不会说改变人。因为我们变得功利,干点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物质、地位上的回报。
当然,在哪个山上说哪个山上的话,可即使是读书真能改变人的命运,我们的学生就真的读书了吗?上大学,不等于一定会读书。在中小学,学生可能只学会了考试,进入大学,有很多学生也是只会考试,对读书毫无兴趣。很多人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拿那个文凭;别说本科,就是研究生,甚至读到博士,也只是会考试而已。读书这点事,他们根本就没学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大学毕业市场化选择也已经有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人才市场依旧不正常。很多笔试、面试更像是形式,只要有一个好大学的文凭,就算有了入门证,然后再有点关系,就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很多大学不怎么样、甚至没有文凭但却有真才实学的人,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也难怪,让进了好大学的学生,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混个文凭。
只读书没有文凭的人就没有出路,这个不正常。学校不正常,用人单位不正常,社会也不正常。
一把香椿
张晓莉
初夏的夜晚,清风徐徐,沁人心脾的清凉让人心生惬意!
饭后带着女儿散步,诉说心事。女儿这个小小的人儿特别懂得如何让你宽心,三言两语略带稚气的话语,就足以令人欣慰无比。
“大妹子,要香椿吗?俺这香椿嫩着哩,又嫩又便宜,三块钱一把。”一位操着浓浓乡音的老婆婆手拿一把香椿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估摸她有六七十岁的年纪,佝偻着身体,一身皱巴巴的衬衫极不协调地穿在她的身上,枯黄的脸色,沟壑般的纹路填满了整张脸。生活的艰辛,岁月的沧桑,就犹如风霜的刀刃利剑在她那张核桃般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不要”,本就不爱吃香椿的我本能地一口回绝了她。可以说,再嫩的香椿也不会勾起我的兴趣,况且这个时节已经是香椿下市的季节了。面对我的拒绝,她只好悻悻地走开了。
我正欲前行,女儿突然用小手偷偷地扯了扯我的衣角,刻意地压低了嗓子跟我说:“妈妈,这个老奶奶好可怜啊!”是啊,这个年龄的老太太们大都在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了,而她却还要为了生计而奔波。女儿的感叹和提醒顿时令我动了恻隐之心。我牵着女儿的手踅了回去,她正欲推着那辆与她的体型、年纪极不相称的“大金鹿”自行车离去,看见我向她走过来,带着满脸的笑意,热情地向我推销她的香椿是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便宜。“买一把吧!”我说。“妹子,就剩下三把了,你就全要了吧!”一点点的为难让我有所迟疑。“妈妈,都买了吧,我们留下一把,给奶奶送去两把!”女儿倒是挺会给我安排。好吧,就按照小家伙的“指示”办呗!
我和女儿提着三把香椿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女儿也在为她今天的善举而欢欣雀跃着。女儿写作业,我在厨房准备第二天的早餐。“这把嫩嫩的香椿炒个鸡蛋也不错嘛!”心里这样想着。然而择香椿的过程却让我感到很不是个滋味儿。外面的那一层还算是嫩嫩的,可是解开那根鲜艳的捆扎的红绳,只见横七竖八的香椿秆凌乱地躺在其中,就那么硬邦邦、直愣愣地躺着,任凭怎样抚摸揉捏,都感受不到一点点嫩嫩的质感。心中顿时笼罩上了一丝异样的感觉,怪怪的,涩涩的。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隐隐地弥漫在心底:现在的人哪,同情和悲悯有时候真的是无处安放,真是一不小心就用错了地方啊!
望着女儿专心写作业的背影,我忍不住一种冲动,想告诉她以后不要滥用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一不小心就会上当;想告诉她有些事情防不胜防;想告诉她不要乱管闲事,以防被心怀叵测之人利用……然而我最后还是忍住了。这一句句声讨如果在她如此幼小的年纪就播下种子,或许在她纯洁的心田上就会长出冷漠、麻木、猜忌、多疑的果子。这既是危险的,又是残忍的。既然善良的种子已经在她心田上种下,那就让这颗善意的种子开花吧,那将是一片美丽的花海!
宝贝,妈妈决定为你守护那把香椿的故事,直到永远!
是啊,世间之人、之事纷繁复杂,我们永远不要奢望别人该如何做,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应该怎么做。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做好自己足矣!想到此,原本纠结的心顿时释然了,我决定选择原谅,原谅那个可怜的老人!
放下的感觉真好,初夏的夜空真美,清明而澄澈!那闪闪烁烁的星斗还是那么亮!微风吹来,扫在脸上,凉凉的,清爽无比,心生醉意!
童年钓鱼
王满刚
俗话说,“吃鱼没有取鱼乐”。水乡农村长大的孩子,小时候都有一本“取鱼经”。有沿着河边一手支着大网兜,一手拿木棒在水里使劲拍打的;有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段破网,往水面上一扔的;有蹲在码头上,在长满青苔的石板下摸“虎头呆子”的;还有三三两两手握钓竿、两眼紧盯水面上几个时隐时现的浮子的……我最喜欢的是钓鱼。
父母怕我掉到河里,打小是不让我钓鱼的,我就像捉迷藏似的偷着钓。刚开始,我只会钓水面上最常见的小白条,我们那里叫参子鱼。这种鱼呈长条形,浑身银白色的细鳞,三寸左右长。夏日河边,总有若干小白条在水面上或悠闲游荡、或来回穿梭,码头上淘米、洗菜、洗碗的人多,小白条更是好往这边聚集。钓这种小鱼很简单,短针弯成的鱼钩在线头上打个死扣,找来一根柳枝系上,便是一套钓具。苍蝇和杨树上到处可见的青虫子,是小白条最爱的美食。小白条贪吃,全无一点警惕,鱼钩往它面前一扔,它拖住就吞,轻轻一提就上来了。如果是一群,钩往他们中间一扔,马上你争我抢起来,一会儿能钓好几条。也有被钓上来又侥幸逃脱的,没多久还来抢钩吃。大人们瞧不上这种小鱼:“细参鱼,没吃头!”我每次都能钓上好几条,每次都趁父母不注意,悄悄把鱼清理干净,擦上盐腌起来。过两天拿出来晒干,烧火时放在锅膛里烤,真香。
村里几个大我几岁的小伙伴,常提着钓的刀子(即鲫鱼)、鳊鱼、青鲲等,得意地从我面前走过。我很是羡慕,不再在门前屋后钓小白条了,好几次跟他们到离家较远的打谷场边、田边僻静处钓,一钓就是大半天,遇上下雨,摘一片芋头叶子往头上一顶(芋头叶很大,呈伞状,我们那里夏天田岸边到处长着芋头),照钓不误。由于我的鱼竿短,又是自制简易钩,大鱼钓不着,舌头丁儿、昂嗤鳞儿、胖皮儿、啰伙儿之类总少不了。每每在中午或是傍晚的炊烟升起后,隐约听到母亲在村里一声一声喊我小名时,我就慌了,急急地将鱼竿往某个草垛边一扔,芋头叶子把小鱼一包,或者直接往口袋里一塞,尽量躲着母亲的喊声往家跑,有几次不幸与母亲撞个正着,后果都一样惨。“麻小和(方言,音huo)!一钓鱼就不晓得回家!”母亲骂着,巴掌就落到我的屁股上。为了钓鱼,我小时候没少挨打骂。
都说清晨鱼好钓,还能钓到大鱼。我们几个常常天蒙蒙亮就爬起来,到打谷场边一字排开钓鱼。我的“装备”也换成了5分钱买的专钓下沉鱼的钩,线是结实的玻璃丝,浮子是用鹅毛杆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穿到玻璃丝上的,鱼竿则是撑蚊帐剩下的细竹子。有一天早上,我早早地到同伴小兵家拿上鱼钩(我的鱼竿一般不敢放在自己家),和他一起到村东的东河口钓鱼。“钓鱼要钓刀子鱼”,刚念叨几句,半沉半显的浮子抖了两下,我心头一喜,耐心等着,结果再无动静,提上一看,钩上蚯蚓早被吃光。如此反复三四次后,我长了个心眼,不时轻轻提提钩,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水下将我连钩带人往河中间拖。我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紧握钓竿,使劲往上提,玻璃丝绷得紧紧的,细竹子弯成了弓。小兵也过来帮我一起慢慢把钩往岸边拖。是一条大青鲲!好不容易把这条大家伙提上岸时,细竹子断了。我抱着这条差不多有我腿长的青鲲直往家跑。在县城工作、平常很少回家的爷爷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见我抱着钓来的大青鲲,先是一脸惊讶,马上高兴得合不拢嘴。“中饭菜有了”,邻居淦二奶奶边说笑着拿来一杆秤,一秤,二斤八两。中午招待爷爷的,是盛了满满两大碗的红烧青鲲。父母没有夸我,也没责怪我,看着他们乐呵呵地边吃边说笑,我心里美滋滋的,比吃鱼还美。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离家也有二十三年。爷爷已不在人世。童年时期钓鱼的往事,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有时也出现在梦里。
走进儿时的小学
孙仁谦
在回老家很紧的几天时间内,是没有到小学校走一走看一看这一项的,却因母亲的逗留,促使我走进了我儿时的学校。
那是盛夏一天的傍晚了,本来就是想到老屋子里找几张老照片就走的,谁知在经过一条曲折而狭窄的胡同口时,母亲却碰上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是熟悉,这人曾是老邻居,一块儿在老屋子那儿生活了几十年,朝夕相处,共度岁月,甚至一闻脚步声就知是谁来了。说是陌生,母亲跟我出门也已有二十多年了,这之间就寥寥地回过几次老家,也是来去匆匆,根本就没跟这些个老邻居照过面儿,只是在偶尔拉话时,母亲还会捎带出老邻居的话题来,末了,总会叹一声,也不知现在咋样了。真的见着了,母亲反而愣住了,只是在来人的身上一个劲地打量,来人也不由得站下了,把母亲也是一个劲地揣摩,嘴皮子簌簌地抖动……
母亲和老邻居站在夕阳下,稀疏苍白的头发,堆满了一层层怎么也拉不开的褶子的老脸上,焗了一层风一吹就能破的红晕,和脚下青苔满布的石子路、身后一家门板龟裂吊着一把锈锁的大门,很和谐地站成了一幅画,古旧却意味深长,落寞却自得其乐,封闭却自享其成。
母亲和老邻居有共同的话题,有属于她们的时代。我勉强地听了一会儿后,就在四外溜达着,一眼就看见了我小时上过学的小学,心想算来也有二十多年没去过了,只听说小学早就搬走了,现在里面咋样了,不如过去看一眼,反正一时半会也走不了了。
跟母亲打了个招呼,就挪步往学校走去。
胡同口与学校之间只隔着一座桥。桥是石拱桥,就一个桥洞子,不知建于何时。桥面只见坚硬的泥土,没有栏杆,桥高约两丈有余,桥下皆是杂石乱草和垃圾。桥面的边缘是两溜儿光滑滑的水泥面,过去没少了坐在上面玩耍,腿就耷拉到桥下荡悠着。
水泥台面儿还在,儿时的玩伴儿没了,个个走南闯北去了,是否还记忆着儿时的梦。过了桥,上了一段儿稍突的土坡,就是学校的大门了。
说是大门,其实就是在一拉长溜教室中间穿了一个洞而已,既无排场的门楼,也无醒目的招牌,几无外人来,村人把牌子挂在自己的心上,那重量可就不可估量了。那时不管家境如何,只要孩子愿上,家长就咬牙也要供孩子上学,否则外人也看不起。
一进门洞,迎接我的是一阵阵刺耳猪叫和一股股刺鼻的猪粪味儿。门洞的地面已经坑坑洼洼,间或塌了几个大坑,两边的墙壁上原各有一块黑板,我没少了在上边挥洒笔墨,现在几无黑板的印迹了。
跳脚走过门洞儿,就是一个很宽大的院子,南北西三面被教室围着,东面站着一座比教室还要高的山丘,俨然就成了学校的围墙。过去院子里黄沙铺地,青砖隔边,里边就是孩子们的天地,之间还有一副篮球架子,不过那是老师们和大人们一试身手的地儿,在山根儿还竖着一根杆子,这是孩子们升旗的地儿,只是在记忆中没想着什么时候升过旗子,只记得在杆子上吊着半截子钢轨,那就是学校的铃铛了,铁棍子当当地一敲,就把孩子们敲进了教室,当当地又一敲,再把孩子们敲出来。
我却站在门洞口不敢挪步了。院子里一大半堆满了黄泥,到处是泥堆被雨水冲洗后遗留下的泥巴,还有一道盘着一道的车印儿,在靠近山根的地儿,还排着一溜儿草垛,有的草垛已经坍塌了,柴草被拉拉扯扯拽出了很大一个摊子,显然是猪拱鸡刨的结果。教室的房子都在,只是门窗皆无,成了一个个黑洞洞,外墙壁斑驳脱落,猪的叫声和尿屎味儿,就是从这些个孔洞中传出来的。
这是我的学校吗?我的学校哪儿去了?一朦眼儿,就觉得同学们还在院子里疯闹,女孩子跳绳的尖叫声还在空中回响,锈迹斑斑的钢轨正在嗡嗡地拖着尾音颤动着,我该进教室了,我快步进了一个屋子,迎面是一面水泥挡墙,里面躺着几头大猪,见人来了,吭吭唧唧地爬起来,把头扛在挡墙上一个劲地叫唤,我悻悻地退着,退着。我一时怎么也无法把一张张笑盈盈的小脸换成一个个丑陋肮脏的猪脸。
真的没了,黑板课桌,一本本折角的课本,一个个陈旧不一的布口袋,还有我赖以频频走进梦境的记忆。
这时,一个妇女跟进来了,打量着问我,你找谁?
我找谁?我也不知我找谁?是找过去自己生活的印迹,还是给现在自己的思想找一个出发点?我颇有几分尴尬,我自己都解决不了的困惑交给她?我自嘲地说了一句,不找谁,进来看看。
妇女很警惕地盯着我,这儿已经卖给我了。
意思就很明白了,这是我的了,你不能随便看了。我只得抽转身子,走出了小学。
母亲和老邻居还在聊着,见我回来了,母亲意识到该走了,就跟老邻居告别,老邻居还有点伤感,也不知啥时还能再见着?这些老房子都没人了,过些年就都塌了。
人老了靠记忆活着,村庄老了就靠历史活着。可村庄没人了,谁再给村子创造历史。那只有一种,老给你看。最后呢?没有答案,也许就是答案……
狮子上树
赵盛基
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草原,一群水牛正在悠闲地吃草,一头饥饿的狮子突然出现在它们面前。
水牛们不知所措,狮子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默默地对峙着。
狮子在等待水牛逃跑,只要水牛群跑起来,自己就有下手的机会。水牛们则更清楚,只要逃跑,跑得慢而掉队的必定会被狮子俘获。所以,它们坚持不动。
狮子实在饥饿难耐,开始慢慢向水牛移动,并发起攻击,逼迫水牛逃跑。水牛也终于忍不住了,开始疯狂逃跑,一头水牛眼看就要被狮子追上。
正当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突然,所有水牛停止了逃跑,掉回头来直视着狮子,一付拼命的架势。狮子一惊,一个趔趄,止住了脚步。
形势发生了逆转,水牛们开始朝着狮子逼近,一头水牛的角差点把狮子顶翻。狮子被水牛的气势吓坏了,仓皇逃窜。
水牛紧追不舍,狮子眼见被追上,它惊恐万状,慌不择路,爬上了一棵大树,这才躲过一劫。
水牛不会爬树,围在树下朝树上的狮子怒吼。狮子大气都不敢出,非常困窘地趴在树上。直到水牛放松了警惕,狮子才悄悄下树。
没想到,草原之王也有颜面尽失、如此出丑的时候。此时的王者,威严不再,尊严扫地。反倒水牛却威风八面,让人敬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征文启事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本报特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征文活动,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投稿。
一、活动时间:2015年6月至9月。
二、征文题材:散文,诗歌,小说。
三、征文要求:紧扣主题,观点鲜明。散文、小说字数不超过2000字,诗歌不超过30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通讯地址、电话、邮编、电子邮箱等,谢绝一稿两投。
三、征文刊发:优秀作品将在本报“柳泉”副刊发表。
四、投稿方式:来稿请发至电子邮箱:rbliuquan163.com。联系电话:0533--3179809
本报文体新闻部
2015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