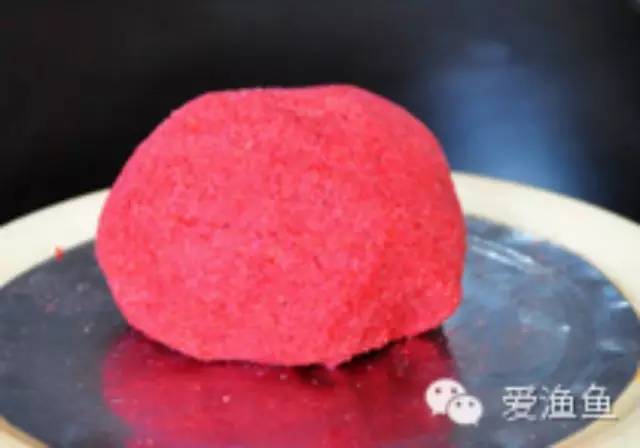撒拉爸
文/马学义
(一)
果真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头割了还到黄河里喝水的筏子客!衣服剐烂了,皮肉擦破了,筋骨扭伤了,他全然不顾,仍跟上一帮年轻人,声嘶力竭吆喝着,粗野地咒骂着,怒冲冲地拳打脚踢着,把一群惊恐不羁的牦牛经狭窄的桥板强行往闷罐车里驱赶。整整忙活了一个后晌,好不容易在太阳落山前把最后一头桀骜不驯的老秃头,前拉后推地硬关进去。撒拉爸撒拉爸:方言,叔叔。这才如释重负地大松一口气,索性席地而坐,一边摘下头上的圆帽扇凉,擦汗,一边踌躇满志地笑着横卧在铁轨上的一长列车厢。
残阳如血,余晖斜射,撒拉爸满脸的胡楂楂被染成了千万根金针,眼角的鱼尾纹活像一对美丽的花朵。看得出,此刻,他心里是稳当而踏实的。
近几年,国家伊协接连组织了几起穆斯林朝觐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条件一次比一次宽。据说,有的省市连卖烤羊肉的穆斯林信徒,也荣幸地完成了朝圣的神圣天职。这一情况可把撒拉爸眼馋死了,不由得梦牵魂绕,私下悄悄做开了准备。他伙同一帮人,千里迢迢,从青藏高原往南海之滨的深圳市贩运蔬菜,收入相当可观。喏!这次又装上了百十头,全是一类膘。胡大保佑,这一回若是一帆风顺,平安而归,手中积攒的钱,也满够他朝一趟圣的。真若如此,那他夙愿得偿,阳世上再没有什么多余的奢望了。
谁能料想,撒拉爸这一圣洁无邪、至高无上的庄严举动,却意外地遭到了他的老阿奶和儿子们的百般阻拦和反对。每每他出去归来,母子几个翻眼噘嘴,喋喋不休地左怨右责,弄得他头昏脑涨,心烦死了。昨日下午家庭对他的“联合讨伐”,登峰造极,简直像孟克尔、乃克尔孟克尔、乃克尔:伊斯兰教信奉的两个审讯神。在地狱里的审讯,使他有口难辩,差一点被活活气死。
“阿爸!”大儿子站在左边炕沿下,指手画脚地说,“你五十大几的人,还这么没命地出门去受苦,叫我们怎么忍心呢?不怕人家取笑?我们儿女的脸往哪里放呢?”
“阿爸!”老二从右边摇头晃脑地说,“钱财好比是粪坑,越深挖越臭。现在咱们家不缺吃不短穿,日子够舒坦的了,你不定定待家干自己的活,却风里来雨里去的活受罪,何苦呢?划得来吗?”
“尕娃们说得对着哩,”老阿奶从门口走到他跟前,慢条斯理地絮叨着,“好马一鞭,好人一句。我们不知说了多少遍,嘴巴都歪了,你个老糊涂,怎么像狼耳朵里吹风,一点儿也听不进?胡大呀,阳世上哪见过你这号没心眼的人,唏——!我问你,别人出门跑外,全是为着拉扯个穷家务,没法子。可你像脚户的骡子,拖把老骨头,呼哧呼哧地瞎折腾,到底为了啥呢?是怕活着没人养?殁了没人抬?唏——!啥怪毛病,狗肉不上架子!”
“砰!”一记猛拳,擂得桌上的盖碗茶水四处飞溅。撒拉爸怒不可遏,双目圆睁,脸色铁青,一双攥紧的拳头,像拳击运动员般平放在胸前,活脱脱一头暴跳如雷的雄狮。看那架势,好像谁要是再敢多嘴,非砸扁了他的头不可。两个儿子骇然失色,小猫似的乖乖缩回原处,低首静坐不语。
老阿奶也顺势侧身坐在了炕边上,缄口无言,只是一股劲儿搓弄着干瘪的双手。惊悸的眼睛不时乜他一下。良久,灵机一动,便拭眼抹泪地说:“怎么了?你个老糊涂,疯汉!怎么连屁臭饭香都分不清,给谁发这么大火哩?你怎么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说呀!唏——今儿个我把话当着一家老小的面说明了,你再这么由着性子跟上那伙年轻人乱跑,哼,我可是没有给‘口唤’口唤:准允,许可,宗教语。着。”
“你……你你你……”这一招真厉害,把个倔强而又在火头上的撒拉爸一下给镇住了。他像一只被斗败的公鸡,深沉而艰难地呻吟一声,耷拉下脑瓜,使劲捋起自己的胡须来。
“呸!畜生们,你们懂个屁!为了朝圣,别说吃一点苦,就是送掉这条老命,有啥可惜的呢?再说,这种美事在过去像我们这号人能梦得着吗?哼!今天你们再敢胡闹,我绝饶不了!”想到这儿,撒拉爸不禁恼怒得跃身而起。左右一顾盼,愣怔了:伙伴们早走光了,无踪无影,太阳也已滚下了山后,天徐徐降下了无际的夜幕。他长叹一声,忙扣上帽,迈开虎步,匆匆往回走。
(二)
黄河下游一座独户庄院,便是撒拉爸的家。
这会儿,撒拉爸在上堂,偎着炕角的被褥,平伸双腿,仰坐在红毡上,用五指梳理着胡须养神,一边慢慢饮着盖碗茶。
外面起风了,越刮越猛,从树梢间发出的啸声,恰似一群饿狼在嗥叫。蓦地,房门吱呀一声开了。随着一股袭人的寒风,一个人缩头弯腰,像幽灵般摸黑跨了进来。等走近一瞧,他不禁有点惊愕,忙坐端身子,捻着胡须,用疑惑的目光鹰一般盯着这个屈尊俯就的不速之客,默不作声。
来者是赫赫有名的市管会张主任。他没有介意对方的怠慢,很从容地将腋下的两包茯茶放在八仙桌上,然后笑容满面、彬彬有礼地说,“撒拉爸,你老人家好吗?”
撒拉爸无功受禄,满脸挂着捉摸不定的笑意,吸了吸鼻气,歪头定定地看着对方,没有答话,仿佛一个观众凝神屏息地静待揭幕后的表演。张主任坐立不是,甚是尴尬。
“哎唏,是张主任呀!”倒是古道热肠的老阿奶闻声从隔房走出来,笑容可掬地擦桌倒茶,唠叨着替他解了窘,“张主任,你这个宰骆驼都请不来的贵客,今儿个是什么风把你吹进我们家来了呀?”
张主任接过盖碗茶,吹了吹,呷了一口水,这才放下碗,坐在八仙桌边的躺椅上,说明了来由。
前几天,东城区李书记的掌上明珠——年仅12岁的小儿子,在黄河边玩耍时,不慎掉进河里,丧命夭折了。李书记老夫妇肝肠寸断,好不悲痛。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念起多年的交情和一片恻隐之心,一齐出动,夜以继日轮流在长达几十华里的河边上寻觅,仍未发现尸体。这使老书记两口子越发悲上加愁,痛不欲生。尤其李夫人,整天发疯般捶胸顿足,号啕不止,一连几日粒米不进,滴水不沾,好多次死去活来。看来要是捞不到孩子的尸体,她定会寻了短见。
张主任说得惟妙惟肖,情辞凄婉,老阿奶听了,忍不住在一旁揪住胸襟,唏嘘流泪了。撒拉爸双手摸了把脸,眯细双目,望着张主任,微微扬了扬下颌,仿佛说:“这事你找我有什么用?我又不卖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真是。”
“撒拉爸,”张主任转动了一下顾盼流利的眼珠,声音艰涩而又柔软,“我不说你也明白,还是行行好,可怜可怜他老两口吧。”
“张主任,”倒水的老阿奶倒吸了一口气,停了手说,“阳世上谁还没有求人的时候。嘿,李书记老两口真命苦,怪可怜的。可是,张主任,你看他这岁数还能下得了河吗?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心里却骂道:“我知道你们这号人从不把荞麦面当五谷待承,在这季节叫一个老汉下河捞死人,哼,畜生!亏你能说得出口来。”
“唉,事在人为嘛。搁了多年的油葫芦,油味仍浓着呢!”张主任端碗,连口喝着,一双颇灵泛的眼睛从碗顶机警地注视和观察着撒拉爸的反应,“这事非撒拉爸再没人帮忙,我看还是给老书记赏个脸好。我敢担保,事成之后,有你们的好处。”
老阿奶没吭声,悄悄走到门槛边,蹲在地上,用盖头捂住自己的嘴角,担心、忧虑地望着老汉。
撒拉爸冷静得像一尊石像,意味深长地沉吟一声,握住胡须,目不转睛地直盯着张主任,心里不由一下勾起了一件不堪回首的悲惨往事……
十多年前的一天,撒拉爸突然被叫到了清队办公室。年轻的张主任凶神恶煞般坐在办公桌前,声色俱厉地审问道:“你在马家军当过兵吗?”
撒拉爸神色坦然,轻轻摇了摇头。
“参加过国民党?”张主任提高了音量。
撒拉爸笑着连连摇头。
“任过要职?”张主任猛一拍案,圆睁怪眼,忽地离座跳起。见对方又在摇头,不由哼了一声,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走过去,目光霍霍,鞋声橐橐。猝然,他停步,疾声呼叫:“阿布都!”
“澳依!”撒拉爸亦大声道。
“哈哈哈!”张主任发出了一阵胜利者的狞笑,片刻,敛住笑声,一咬牙,“啪!”甩出一记有力的耳光,“啪!啪!”紧接着又是两记,然后手叉腰,用脑瓜划着圈,唾沫四溅、歇斯底地里吼道:“哼哼,撒拉爸,屁!他妈的,装得倒像,哼哼,你个狗的不是没有姓名嘛,嗯?你并没有忘记它嘛,嗯?”
撒拉爸愣了一阵,双眼喷着怒火,握紧拳头,像下山的老虎猛扑过去。但未及接近张主任,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抓住了他的双臂,又跑出两个人,左右开弓,拳打脚踢了一阵,便五花大绑起来。撒拉暴跳着,挣扎着,嘴里骂声不断:“你们想干啥?我就叫阿布都嘛,你你……你为啥打人……我犯了什么王法……你个畜生……”
“说得倒好听,”张主任歪着嘴,斜着眼,阴阳怪气地说,“不是说撒拉人中14岁以上,50岁以下的全都当过兵吗,大部分还是连级以上的官长呢,怎么单你一个逃脱了呢?嗯?”他很神秘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仿佛抓住了对方的生命线,抖了抖,“阿布都,你睁大眼好好看一看,白纸黑字,一清二楚。哼哼,你想滑掉?妄想!只有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才有你的出路,不然,哼哼……”
阿布都这名字别说是在撒拉人中,就是在整个穆斯林信徒中也简直多如牛毛。撒拉爸脸上并没有刻字,凭什么认准那纸上的阿布都肯定是他,而不会是别个阿布都呢?可怜他个撒拉爸有口难辩,被戴上帽子,蒙受了长期的不白之
冤……
尽管事过多年,但记忆犹新,一旦想起,他就不由得怒火烧心。撒拉爸像吃了颗酸杏般皱紧面孔,剧烈抖动了一下脑瓜,瓮声瓮气地说:“李书记自己为啥没有来?”
“撒拉爸,”张主任眨眨眼,煞有介事地说,“这时刻,他老两口不伤心死算好了,还能出得来门吗?撒拉爸,你看这事……”
撒拉爸嗽嗽嗓门,鄙夷地睃了一眼,正欲奚落他一顿,蓦地,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起来。他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赶紧跳下炕来,顺手拿起一条毛巾搭在肩上,又接过老阿奶端来的汤瓶,头也不回地进隔房净洗去了。
张主任一接到这无声的逐客令,知道再等也无用,只好站起,败兴地垂头而走。
(三)
“撒拉爸”,并非是真姓实名,也不是什么绰号。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自然因为他是个撒拉人。但也不尽然。在这拥有几万人口的小市镇,从古到今迁徙来的撒拉人,为数不下几千。他们为人敦厚、诚挚、乐善好施,颇受人们称赞,可是一个也没誉得“撒拉爸”这一称谓。不言而喻,在这极为平凡的称呼中,必定有它特殊的情由和内涵。这不得不提及他孩提时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一个寒冬腊月的中午,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冰凌莹莹的黄河边,一个瘦骨嶙峋的娃娃,披件油渍渍的短皮褂,静静地蹲在一块大石头上钓鱼。忽然,有一大帮人,喧喧嚷嚷来到了河边。其中一个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人,用拐杖指着河面,吐着大团热气说:“你们准备吧,木头快下来了。捞出一根,半块大洋,当面付清,绝不欠账。”
人们被馋得直吞涎水,一个个撸臂挽袖,跃跃欲试。可是目光一触到那冰碴沙沙作响的河流时,不觉一阵心惊肉跳,头皮发麻,抓大钱的欲望,顿时全溶进那一泻千里的滚滚河水。
这时一根木头乍隐乍现,从上游漂了下来。老板一见没人动弹,便高声举起手杖,慷慨地抬了价:“好,一根一块大洋,看谁先打头阵。”
人们像是要进屠宰场,皱眉蹙额,慢慢往后缩。老板急了,抓耳挠腮,团团乱转。眼看木头要淌下去,他一咬牙,瞪大双眼,跳起来说:“他妈妈的:钱财是狗屁!老爷今儿个豁出来了,不心疼了,谁下?一根两块大洋!”
“……”
“三块!”
“扑通!”话犹未了,一个人早跳下河去。大伙惊骇万状,拥前一瞧,但见那个人强劲地划动着双臂,像一支离弦的箭直向河心的浪峰射去。不大一会儿工夫,便推着那根木头回游了。当他上岸时,大伙儿不禁失声叫起来:“啊!是你?撒拉娃?”
年仅13岁的撒拉娃,未及人们定过神,又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捞那淌下来的第二根木头。不知一个羽毛未丰、乳臭未干的憨娃娃哪来的那胆量和力气,也不知他身上藏有什么御寒保温的神器法宝,在砭骨的冰河里,竟一口气捞出了8根木头。
从此,撒拉娃闻名遐迩,妇幼皆知。
(四)
经一夜疾风的撕扯,满天的乌云跑得不存一丝,天空一片晴朗,湛蓝。火红的太阳从轻纱般的朝霭中冉冉爬上了嵯峨苍莽的山巅。秋末冬初的高原山川,分外雄伟瑰丽。
一帮不知忧愁的年轻人,高门大嗓,粗鲁耍笑着走远了,不时回过头喊一声,“喂!撒拉爸,快走呀!”
“你今天是怎么啦,老汉?快些走哇。”送行的老阿奶,忍不住也催促起来。
撒拉爸慢腾腾地迈着步,双眉拧得很紧。间或停下来喘喘粗气,按按肩头的褡裢,喟叹一声。
昨夜他几乎没合眼。临睡前,母子几个又跟他纠缠不休。
“阿爸!”照样是大儿子坐在炕左边先打头阵,“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为了一具尸首,竟拿生命去冒险,这值得吗?有那个必要吗?不错,你是个有名气的筏子客,可是也不能忘了:好猎手山崖上摔死了,好水手河水里淹死了。阿爸呀,你怎么越活越糊涂了。”
“阿爸!”老二接上说,“阳世上行善积德,不仅完全应该,主要的还是我们穆斯林的本分。不过,这还得看个对象了,给张主任那类人行好,别说是我们,哼!怕大慈大悲的胡大都不乐意呢。阿爸呀,难道你真忘了咱们家蒙受的奇耻大辱吗!”
撒拉爸的心“咯噔”跳了一下,但他立刻镇住了神,没有上火,倒悠闲地搓动着一双赤脚,捻着胡须,高深莫测地笑望着他们频频颔首。心里说:“憨娃娃们,你们懂个啥哩?十年动乱时,人家共产党的那么多大干部,受了多大的灾难哟,有的还丢了身家性命,多冤枉呀!可并没见他们以牙还牙呢,好端端地仍为咱百姓们操劳。那才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嘿嘿,咱小小个平头百姓,受了屁大点委屈嘛!算个啥债。已经过去了的事,就当它是一场梦,干啥要老挂心头,折磨自己呢?哎呀,我的憨娃娃们哟,你们什么时候才挖得清……”
“哎,我说老汉,”老阿奶像是揣到了他的心思,正色地说,“你不必再瞒我们了,你那几个冒失鬼全给我说了。你呀,唏——这么大个正经事,要是早说明了,谁个还拦呢,唏——我们娘儿几个又不是吃草长大的,心眼再怎么死,这么点道理总还挖得清呢?唏——好了,明日个你放心上你的路吧,胡大保佑你平安无事。这一趟回来,若是钱还不够数,你再不用跑了,家里哪怕砸蜗卖铁、拉账背债,总得保你朝圣呀。”
信念,圣洁的信念,至高无上的信念啊!它一旦被树立,必然与人的生命紧紧相连,与灵魂融为一体,什么力量都休想撼动它。这时的撒拉爸,纯真、净洁和敦厚的心灵全被那神圣的信念主宰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直感到自己确实老了,该抓紧准备朝圣的钱了,再没那时间、没那力量下河折腾了。心一灰,双目渐渐合拢了……
“你走快些行不行,晚了要误车的。”老阿奶着急地又催了一声。
“嗯,嗯嗯。”撒拉爸漫不经心地应答着,但步子仍没有加快一点。他陡地停了步,怅然若失而又负疚地摇头沉吟一声,双手慢慢地实实地摸了一下吊长的脸膛,暗暗在忏悔:“至贵万能的胡大呀,你可作证,不是我阿布都心黑可恶,不愿修桥补路,实在由不得啊,求你饶恕我吧!”于是,他的心灵稍稍得到了一些抚慰,眼前亮了很多,便提起神,放大步子追了上去。
(五)
“撒拉爸!”
“撒拉爸来了,看!”
撒拉爸闻声惊异地抬起头,一看,发现自己已经上了黄河桥。伙伴走远了,不见一个身影,他狐疑地四下一扫眼,观见桥下河边上,有几个人正在做下水的准备,那个张主任伸长脖颈,木木地向这边张望。
一会儿,一个水手跳下了河,但他挣扎了一阵,没游进漩涡处,就被几个浪头连连打回,顺着湍急的河流淌下去了。撒拉爸惋惜而责怪地摇头叹了一声。
又一个水手跳下去了。但他不知为何,双手惊慌地乱扒拉着直往下淌,无疑呛了好几口水。要不是另一个水手及时跳下去,奋不顾身地将他拉出,险些送了一条命。
撒拉爸叹了一口气,攥紧胡须,眯细双目静静地俯瞰着咆哮、怒吼、腾跃的浩渺河面。此时此刻,他心里也像那滔滔的黄河水,掀起了情感的层层波涛。
漫长的岁月,在这条河上,他不知搭救过多少条生命,打捞过多少具尸首。大凡有人登门相求,他绝没二话,一拍胸,欣然应诺,从不索分文酬谢,只求人们打开金口,衷心地为他祝福一句就够了。正因为如此,他才那样的享有盛名,深孚众望。可是,为什么单就这一回……他的心灵震颤了,神经绷紧了,仿佛有无数双含着轻蔑、鄙夷、嘲讽、耻笑而又等待、央告和鼓励的目光盯着他,任他快做抉择。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心里怯怯地问自己:“你今天是怎么啦?人活着行善,其功德比殁后超度可不知大多少倍了。眼下对偌大个灾难却无动于衷,你究竟有什么资格去朝圣呢?”想到这儿,他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下撂掉肩头的褡裢,鬼使神差般拔腿向桥下奔去。
“哎哎,你到哪里去?”老阿奶不解地眨巴着眼,大声问。立即,若有所悟地倒吸了一口气,毛发悚然,脸色刷白,着魔般飞跑过去,一把拽住他的衣摆,“你你你……你疯啦,快赶你的路去……”
撒拉爸没有理睬,猛一甩手,挣脱她,头也不回地飞步而去。
老阿奶没防着,趔趄几步,摔倒在地,丧魂失魄地扬起手喊叫不休……
河边上一片死寂。空气凝固了,老阿奶的心似乎也停止了跳动。她睁着一双死鱼眼,灵魂出窍般凝视着模糊不清的河面。撒拉爸一头扎进河里,半晌没见他露面。又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任何动静。这一下那几个水手也一个个张口结舌,相顾失色。连张主任也吓得紧皱双眉,扁紧嘴唇,来回走动不止。老阿奶面如土色,下颌垂落,十分吓人。
突然,河面上“哗”的一声响,一个人头拱水而出。但见撒拉爸摸了把茬茬胡,像条鲤鱼,穿过房顶高的浪峰、山谷似的漩涡,直向岸边游来。
几个水手欣喜若狂,一蹦几尺高,大声喊道:“啊哈,筏子客,英雄!”“撒拉爸,英雄!”
老阿奶如梦方醒,定睛瞧了一阵挺立在河边的老汉,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一酸,禁不住洒下一串清亮的喜泪。但,最为高兴的还是张主任。
蛇爬的洞蛇知道。前一时期,有个大走私犯被张主任发现,跟踪追击。那家伙眼看被他擒获,趁天黑不辨,将一袋贵重的赃物狠心扔下了漩涡里。今天,撒拉爸竟把它捞上来了,他自然喜不自胜。
“撒拉爸,”等打发走那几个水手,老于世故的张主任面带诡谲、得意的微笑,走近全神贯注注视河面的撒拉爸,低声说,“好啦,你不用再下去了。”
“嗯?”撒拉爸像是没有听清,忙转过头,隆高眉头,大惑不解地死死盯着他。
“你不就是凑万把块钱,想朝一趟圣吗,嗯?”张主任仿佛掌握着一种能征服人心的神秘符咒,从容不迫、和言细语地说。
“这……”撒拉爸越发被弄蒙了,半张嘴,眨巴着眼,等他下面的话。
“喏!”张主任冷笑一声,朝那袋子一努嘴,使了个眼色,轻松地说:“把它捎上车去,到深圳,自有人来接。”
啊!原来是这样。撒拉爸心里全明白了。像当头打了个炸雷,两耳嗡嗡作响,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几乎昏厥过去。他的率直、笃实、善良受到了欺骗,人格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莫大侮辱,筏子客的尊严和声誉遭到了不能容忍的亵渎和践踏。顿时,他狂怒得七窍冒火,浑身发抖,眼睛睁得如铜铃一般,两条长臂伸出来,10根手指剧烈颤抖地分开着,犹如老鹰的双爪。看那架势,张主任无疑将会被他撕成碎片。
“撒拉爸,这大可不必了,”张主任神态自若,平静地说,“这事你知我知天知。时间不早了,快带上它上车吧,事成之后,有你的好处。那朝圣的事,你放心好了,我张某全给你包了,嗯,怎么样?该满意了吧?”
“呸!你这个魔鬼,畜生……”撒爸拉一把揪住了他的胸襟,用力晃了晃,气得再也说不成话。
“去去去!少在这装洋蒜,你给我放干脆些,到底成不成,嗯?”张主任仍不松口气。
撒拉爸灵机一动,鄙夷而憎恶地瞪了他一眼,慢慢松开了手,旋即,一转身,抱起那袋子,像是中了风魔,向河里走去。
“哎哎,撒拉爸,你到哪里去……”张主任一下惶恐了,向前跑了几步,忙不迭声地支吾。撒拉爸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回头冷笑一声,朗朗地说:“畜生,你知道吗,嗯?古拉亥古拉亥:耳朵,喻信誉、尊严。比什么都贵重!哼,畜生!”说完,直向河心游去。
张主任如丧家犬,一下跌坐在地上,眼睁睁望着远远游去的撒拉爸,不由喃喃自语:“筏子客,古拉亥,筏子客,古拉亥……”
注:原载于《青海湖》1990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马学义 撒拉族,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1937年12月出生。青海省文联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
1957年7月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政治系。1980年调至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1986年调到青海省文联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
出版过撒拉族民间故事集《骆驼泉》、民族大家庭丛书《积石山下撒拉家》、民俗丛书《撒拉族风俗志》(合作)、中国民间文学故事大系《土族、撒拉族民间故事选》(合作)。《骆驼泉》获全国民间文学优秀作品三等奖。
1986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发表过中短篇小说《鲁格娅》、《命运的呼唤》、《哈三告状》、《撒拉爸》、《花儿皇后》等10多篇,电影文学剧本《苏四十三》。《撒拉爸》获青海省建国四十周年优秀文学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