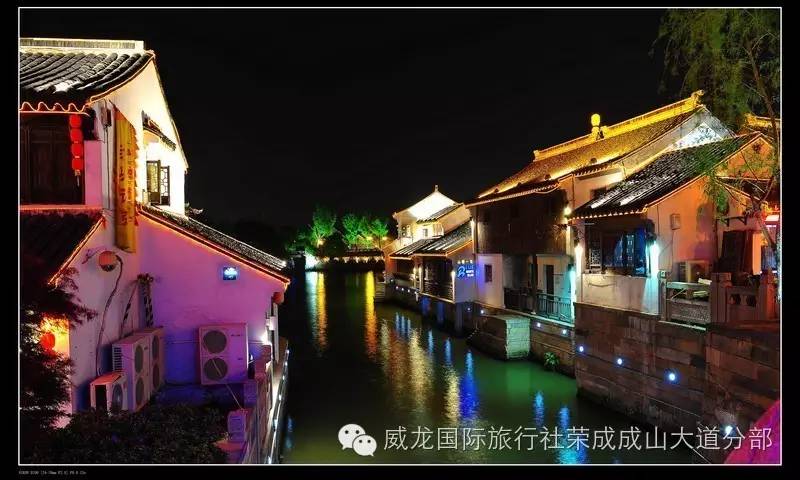你很难不感受到当下政治气候中的寒意。过去 12 个月间,世界似乎倒退了几十年——仇恨运动和民粹社团正迅速成为不少西方社会的标配。我们习惯了看到世界由一群越来越稚嫩的面孔主宰,而父母不再可能是预防下一个杀手的良药。在英国, 2016年的退欧投票震惊世界,与此同时,基于种族仇恨的犯罪率上升了五倍。在美国,唐纳德 · 川普以其右翼言论赢得了惊人的呼声。
光头党给我归属感
对Christian Picciolini而言,这些地震般的政治转变不应该被忽视。作为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他在伊利诺伊州蓝岛市出生和长大,直到1987年加入芝加哥地区的第一个光头党(CASH)时,他还不到14岁。当时这个组织只成立了两年,组织的头头Clark Martell(当然是光头)在街上偶遇了他——如同一个小混混遇见另一个,前者从他嘴里抢走了烟头,然后说“我要拯救你”。

少年时期的Christian Picciolini
如今,Christian Picciolini每次提起这次的经历时都会发笑,大概是因为它听上去太像一出肥皂剧里的烂俗情节了。可对那个精瘦、寡言的14岁小子而言,加入光头党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从没有见过像Clark Martell的人,看到后者的第一眼,他就知道那是他想成为的人。做生意的父母向来对他疏于关心,而这种缺失,很快在由年轻的“边缘人”组成的光头党里找到了替代。他们提供的情义和信任成了他在社会面前最强的纽带,而随着和父母的疏离,他和光头党的联系也越来越深——

Christian Picciolin在达豪集中营的“到此一游”照
在穿着印有White Power的T恤衫和打着卍字补丁的尼龙夹克四处招惹麻烦之余,他开始出席集会,带着自己的乐队(之一)Fnial Solution录制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白色音乐”,在德国魏玛的一场新纳粹音乐节上演出。

Final Solution成员在魏玛的合影,因涉及肖像权,发布时该组织手动添加马赛克
8年后,22岁的Picciolini成了CASH的头头儿,这简直称得上一个另类的成功学故事。随后,他将芝加哥的组织并入了羽翼未丰的“锤头国( Hammerskin Nation)”——当今最危险和最暴力的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组织。
退出光头党的“民族叛徒”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信仰”开始动摇。现在,在昔日同伙中他被称为“民族叛徒”。2010年,他的弟弟被暴力夺取了生命。不久,一次“百无聊赖”的夜间行动后,他和同伴们在一家麦当劳偶遇了几个黑人青年,口角迅速升级成搏斗。在对一个已经血流满面的黑人男孩拳打脚踢后,他忽然觉得那男孩长得很像他的弟弟……随后,他退出了光头党。

Christian Picciolin的纹身还保留着他“逝去的青春”
经历了四年的低潮期,离婚、吸毒、酗酒、破产,之后又奇迹般的重生了——他写完了一本名为《暴力罗曼史:一个美国光头党的回忆(Romantic Violence: Memoirs of an American Skinhead)》的自传,并成立起了“恨后重生”——一个非营利的和平组织,致力于打击极端性质的仇恨向公众传播。其后,“美国出口(ExitUSA)”项目也于2015年启动,旨在为在这类组织里的人们提供逃离帮助。如今的Picciolini,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电视制片人,他有自己的媒体公司,曾被任命为芝加哥格莱美摇滚委员会成员。如今,再见到这个发福的中年大叔时,没有人会想到,他曾多么仇恨这个世界。而在网络上,各类种族仇恨组织的网站也已经取代了曾经的一对一招募,让这个世界看起来越来越远离他的理想。

2003-2015年,美国的仇恨组织数目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我有很多的遗憾,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被我伤害了身体和情感的人。我也把很多人招募进来,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弟弟在一起,他以我为榜样,跟随我的脚步,以暴力寻求我的注意。”
“他后来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而被谋杀了,如果我当初能阻止他——如同我希望当初能有人阻止我一样——他也许不会死。我十分悔恨自己栽在那些年里的种子。如今我离开光头党超过了 20 年,仍然没能完全清除自己的罪行引发的恶果。我对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发生的白人极端主义暴力事件都有种负罪感。”
Christian Picciolini在YouTube上的自述短片
“虽然我不可能亲自消灭他们,但我唯一能做的是,用我的经验帮助释放和消减我也曾有的那些邪恶的想法。语言和信仰都产生后果,但也会有积极的一面——我知道我的过去塑造了我的现在,我为目前的工作准备了很多年,如今我愿意直面曾经创建的那些有关仇恨的叙事。”
“恨后重生”援助离开极端组织
“现在想来,也没有那么一个特定的时刻,让我决定离开。我在那里生活了八年——这是我作为一个小伙子唯一知道的事情。但有一系列事件在挑战我的底线,并一点点改变我。第一件事是孩子的出生。当有实实在在的人可以让你再爱一次的时,“恨”就滑入了反思的列表。大约在我第二个儿子出生时,我决定开一家小型的唱片店以便我能卖掉我曾经参与制作的那些‘白色音乐’,这是第一次有人在主流零售业里支持极端运动,特别是通过音乐。那段时间,这些音乐的销售占了我收入的 75%,光我自己乐队的唱片就卖出过两万张。
后来我也开始卖重金属、 朋克、斯卡乐、 嘻哈和其他类型的音乐。那些迈进我店里的人,有很多我曾经仇恨的对象,但通过交谈,他们的故事渐渐地把我从以前的圈子带出来。我发现我们是相似的——一旦这种连接建立起来,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为原来的仇恨找到正当的理由。”

美国活跃的种族仇恨组织分布图
“每个曾受到孤立的年轻人都可能被极端主义吸引,隔离、 恐惧、 自卑,他们的心理弱点都会被精明的招募者轻易攻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关心,被尊重。有些人通过其他的工作获得这种感觉,而有些人,如我,则陶醉在暴力行为带来的支配感里。但暴力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表达,只是因为其他选择在直接而冲动的暴力面前很容易被忽略。”
“但成为了极端组织中的一员,就意味着你必须遵守他们的规矩,完全浸入一套严密的逻辑法则。很多人甚至在自己的“信仰”破灭后仍然无法离开,不仅仅是出于避免危险,也是害怕面对失去了一切曾经所拥有的人生,不得不重新开始。”

“‘恨’来源于被忽视。恐惧是父亲,孤立是母亲。因为孤独,你害怕未知的世界,会轻易相信招募者对“天堂”的许诺,后者将你的处境归罪于他人。如今,我们甚至看到川普和一些极端的共和党人通过相似的方式向民众发言,他们没有制造新的种族主义,只是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平台,让他们自然生长,趋向合法化……川普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理想代表。有时,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抄袭我90年代初在集会上的讲话,只不过用的是一套更悦耳的词库。”
“我参加过一个在芝加哥的川普集会,后来因为抗议活动取消了。在一个体育场里,聚集了 3000 名川普支持者,我目睹并听到了一些比任何光头党或三K党能说出的的更卑鄙和很肉麻的种族歧视语言,而这些人看起来就像我们熟识的邻居、牙医及教师 。”

CASH岁月
“9·11 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死于种族至上论者之手。成立‘恨后重生’的想法诞生于2009年,我和一个同事——另一个前新纳粹的光头开始写一个博客,记录下自己作为一个光头党前成员的故事。当时,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帮助人们从白人团体中退出,而我们对这种困难有最真实的体会——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建立这样一个小组。”
“‘恨后重生’的工作人员全部由前极端主义者组成,我们不仅照顾那些想要开始新生活的人的心理状况,还会在教育、工作培训上给他们提供帮助,甚至在必要时为他们清洗纹身。”

“不下判断,去援助;如果你准备好告别仇恨和暴力,我们准备好了提供帮助。”
“我们目前对待极端主义者的方式就像创可贴一样直接但不可靠,伤口仍会感染,细菌仍会扩散。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世界,不仅仅是在美国,不仅仅建立在肤色差异上——我说的这些话,过了20年我仍会一字不差地写下。”

本文由摩登天空杂志原创,转载请扫下方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