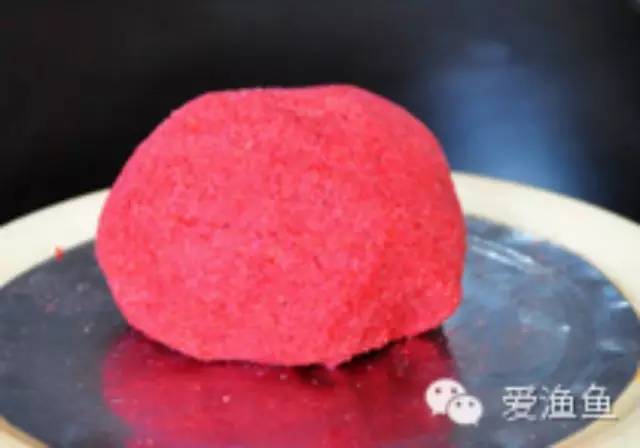新哥在养猪之前,从六岁开始便在靳江河畔养鸭。他有一个很铁的“鸭友”(一起放过鸭的朋友,简称鸭友),住在江湾的王哥。王哥于十五岁转行,后在靳江河捕鱼为业,成了靳江上的“渔司令。”从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江湾的“仇三猛”及道林的 “红旗大队长”,都曾是王哥的手下败将。十多年前,电打鱼风起云涌,鱼越来越少,王哥的二哥还不幸因电鱼殉职。自此,王哥义绝江湖,在长沙做起了门面招牌生意。

我想探寻靳江鱼况,便由新哥出面请了王哥。王哥二话没说,抄起双桨便跳上了船。







新哥说靳江河这一段其实铺了很多地笼,只是在水深的地方我们看不见。地笼一则用来关鱼,二则用来捉龙虾。河里鱼不多,但密密麻麻的尽是龙虾。龙虾非虾也,那正宗的河虾呢?王哥摇着头:“河虾早年被‘敌杀死’搞得差不多,后又碰到电打鱼,都要搞绝了。老子要是再碰到搞咯号路的,老子砍断他一只手!”王哥用桨狠敲了下船舷。“这龙虾其实不是好家伙啊,打的洞有一尺深,河坑都打松了。它什么家伙都吃,连‘革命草’都被它吃光!”我想起新埠头往下赶的“水葫芦”,不知龙虾会否爱吃。实质上,“革命草”和“水葫芦”,都曾是猪的爱食。但猪都改吃饲料了,况且,也没人再来扯了这些草去煮给它们吃。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简称:CSWCA,成立于2004年。致力于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开展自然环境教育和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旨在用行动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