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福借钱
崔国哲 (朝鲜族)
陈雪鸿 译
苦苦等待的国庆节黄金周终于到了,需要准备的东西十分繁杂。除了钓鱼器具之外,还要准备帐篷、垫子、燃气炉、小锅、米等东西。在准备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时,早就等候在楼下的钓友们更是接连不断地催了又催。
马上就来——几次食言后正打算出门时,电话铃声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就说我不在。对着正要去接电话的妻子,我号令般地扔下一句话后转过身去。十有八九是找我的电话。
南大川?现在正要出门呢……好的……哎,好像是鱼塘找你。
该死的……鱼塘找我……看来妻子已经知道我们这次又要去南大川钓鱼。等等,会不会又是曰福来的电话呢?
我不情愿地接过电话,在确认了把话筒震得山响的特有声音后,没有猜错的轻微放心和这次会不会又是借钱的隐隐不安在同一时间里不约而至。既然是花工夫打来的电话,肯定是有所祈求。
嗨嗨嗨嗨……你正要出门去钓鱼,我这电话也许打得不是时候吧?
曰福特有的大嘴和嗨嗨嗨嗨的清脆笑声,仿佛不是来自话筒,而是在旁边耳闻目睹一般。
办公室里的同事从来不提曰福名字,总是用嗨嗨嗨找你,嗨嗨嗨又来电话了来代替。看来曰福特有的嗨嗨嗨颇有人气。
有什么事情呢?还装得那么客气……然而,曰福似乎并不认为是客气,而是直接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
既然知道不是时候,我本不应该打电话。
本来就不应该打嘛,此话从我嘴里脱口而出。与曰福说话绝不能文质彬彬。假如在交往中像书呆子那样客气,像共青团书记那样谦恭的话,反而是更糟糕的事情,所以必须使用强硬口气。
嗨嗨嗨,我今天结婚,你挤出一天时间来当我的傧相吧。我们村子太穷,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能用的家伙。
什么?你今天结婚?
夜半闻梦语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吧。
怎么?我就不能结婚吗?嗨嗨嗨嗨。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这样的消息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呢?而且又是在当天……
嗨嗨嗨,都怪我老是给你添麻烦,所以没好意思事先通知你……实在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才厚着脸皮来求你。你大人不记小人过,赶快来吧,我等着你。
说完,他不等我答话就挂断了电话。哈哈,这可是太让人为难了。而且,曰福结婚,我为什么非去不可呢!
怎么啦?
妻子生怕自己接了不该接的电话,担心我会责怪,所以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我,见我接完电话后满脸不快,更是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脸上充满了狐疑和担忧。
曰福要结婚了。
曰福?曰福是谁?
就是南大川的曰福,嫂子的堂兄弟……
哦,嫂子的堂兄弟……曰福?结婚是怎么回事?
结婚就是娶老婆呗。
哦,也就是说他一直打着光棍?
妻子在城里长大,对乡下一无所知,光听说乡下未婚的小伙子正在盲目地等待机会,却从来没有真正用心去想过。
太可怜了,真是人到四十刚找到另一只袜子啊。
南大川位于延吉通往珲春的路口。
这是哥哥岳母家的村子,并不是一个被认为太过荒凉的地方。虽然不像其他村子那样村后是梨树之类的山林,但是也背靠丘陵一般的小山,村前有一条一到旱季就变得像黄牛尿一样流淌的南大川。我曾随哥哥去过几次,认识嫂子他们家住的村子。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别的事情要在南大川与谁相见。这在我命运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那是我到报社后不久,同事来电话说有人找我。那天,我正外出采访,来电话时采访还在进行,因此有些不高兴地回了一句以后再说,就挂断了电话。不料同事又打来电话说找我的人根本没想走,非要等下去不可,还说自己是从南大川来的。
南大川?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南大川并没有人认识我呀,即使有人认识我,也只有日子过得不富裕的嫂子一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催促的女同事还画蛇添足地告诉我,那人说是我亲家。看来无论如何也得回去看看。
倒不是因为女同事催促,而是因为中午时间让一个陌生人独自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有悖于我们单位的风格。于是,采访一结束,我就径直返回报社,途中一直被难解的疑虑折磨着。
南大川的亲家?要说亲家,只有从嫂子那里论的那些……会是谁呢?
等我心急火燎地赶回办公室,见到的是一个陌生的乡下男子。而且还是个谢了顶的长得像黄牛一般又粗又壮的男人。
他一见我,就像见了熟人似的嗨嗨嗨嗨……一阵连发,倒也引起我一番好奇心,可紧接着的却像是后脑勺被击中一般的感觉。
你终于来了。听说你不写小说,干上记者的行当了?嗨嗨嗨……你不认识我了吗?
对于这劈头盖脸的戏谑,我顿时拉下脸,气得说不出话来。记者的行当?这口气似乎与小偷的行当相提并论,让人听了感到恶心。
这是谁?说他无礼,还不如说更像是恶毒攻击。我不是什么贵人,记忆力也没到太差的程度。但是面对像路标似的挺立在眼前,接连发出嗨嗨嗨的声音,脸色丝毫不变,说话难听的陌生人……反而觉得自己似乎矮了几分。
还没想起来吗?我是曰福,南大川的曰福。
曰福……曰福是谁?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和民哲姐夫一起到南大川来过吧?你真的想不起来了?我们还一起喝过酒呢。在像乌鸦群飞过西山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记忆里,我只记得和哥哥一起去南大川钓过鱼,根本不可能记住嫂嫂家那些亲戚的脸和名字。
不过,既然是称呼哥哥为姐夫的亲家来找我,还是应该尊为上宾,好好招待才是。
曰福从我恭谦的神情中似乎断定已经认出自己,重新发出嗨嗨嗨的笑声。听着这不合时宜的无聊声音,我不由得又为他的来意感到疑惑。
嗨嗨嗨嗨……姐夫和姐姐不在,我到延吉来一个人也不认识……挺不好受的。
哥哥和嫂子外出打工已经三年了,也难怪他会感到难过。
你找我有什么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就直说了吧。虽然很难出口,但是到延吉来一趟不容易,得寻思好几天。你能不能先借给我300元钱?
什么?借钱?
听了这荒唐可笑的请求,我却笑不出来。这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家,竟然向根本记不起他是谁的我开口借钱!对于他的勇气和竹竿般的强韧,我只有呆呆发愣的分儿了。即使是官方通告也有一定的格式,更何况向人开口借钱。结果他竟然会表示得如此坦然和直白,连客气一番的程序也被完全抛弃了。尽管我憋了一肚子火,却难以发泄出来。即使不看哥哥的面子,就是看在嫂子的面子上,我似乎也应该表示谅解才是,更何况数额也不多,才区区300元钱……我首先想到的是不应该拒绝。
我不露声色地从钱包里慢慢抽出钱递过去,还轻轻地说了一句一起吃午饭的客套话。真是没事找事……话一出口我就暗暗后悔,但是在连客套话也当真的曰福面前也无法改口。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甚至连客随主便之类的礼节也省略了,反而建议去面食店,说是自己喜欢吃面食。
完全是一副主客颠倒的景象。
对此,我没有感到惊讶。既然拥有理直气壮向素不相识的亲家开口借钱的勇气,那么在饮食上也不会例外。
我们在人声鼎沸的加州牛肉面馆里要了两碗牛肉面。
曰福说是头一回吃加州牛肉面,用不干净的袖口不停擦拭着光秃秃额头上不断冒出来的汗珠,呼噜噜、呼噜噜地吃得十分热闹。我偷眼瞧着他的吃相,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丝恻隐。正是这样的同情,维持着后来我与曰福的交往。不过,当时我并不清楚这同情的含义。
从惊讶到同情虽然只有一个小时的过程,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模模糊糊的梦。同情来自于曰福狼吞虎咽般地品尝头一回吃到的大众饮食加州牛肉面,来自于我偷眼看着他不干净的衣服和后跟塌落、样式过时的黑皮鞋。他也应该是一个心中有着乡下温情的人,要不是出于无奈,怎么会来找我呢……我不由得产生了宽宏大量的理解。我们两人像瞎子杀鸡那样,坐在那里默默无言地埋头吃面。只有曰福近乎于夸耀的自我介绍,才会时而打破餐桌上沉闷的气氛。据他说,虽然住在乡下,但是并不干农活儿,而是从事什么技术性职业。在乡下能从事什么技术性职业呢?连乡下出生的我也不了解……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只是开始而已。
几天以后,那笔钱通过邮局返回到我手里。说实话,我给曰福那笔钱的时候只当是被骗走,因此心里十分坦然,并没有抱着什么期盼想法。然而,当那笔钱真的又回到我手里,不仅让我十分感动和惊奇,同时也让我又一次想起了曰福。他竟然像海市蜃楼一般出现在我眼前,使我仿佛重新看见了他一口气吃了三碗加州牛肉面的情景。
对于我来说,曰福经常出现在面前,既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不快的事情。
据他说自己是南大川砖厂的一名技工,但确切地说只是干一些摸摸绞车开关、给手推车轮子打打气等杂活儿。这些大致上就是他所说的技术性职业。尽管如此,他依然像算命的那样大言不惭,似乎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通晓。
乡下一般把这种人称之为“大炮”,依照曰福的吹牛程度来看,我觉得他完全够得上“大炮王”的美称。他自称拥有被认为是乡下最为华丽的经历,曾是煤矿井下工人,又在铁匠铺敲打过几年铁砧,还干过贴瓷砖、铺瓦、木匠等活儿……总之,是个“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他甚至还神气活现地夸耀说,按理说自己早应该是个有实力的富人了,只是因为身边既没老婆也没其他家口,所以从不知道把口袋里的钱存起来,都挥霍在吃喝玩乐上了。
每当我快把曰福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就又会找上门来,一般不是借钱就是来吃加州牛肉面。他总是说我像个对人不冷不热的人,实际上我对他也的确如此。就这样,我与曰福的交往越来越热络,但这种交往并不像铝那样柔软,而是像生锈的钢铁那样生硬粗糙。他十分讨厌凡事讲什么礼节和规则。
与他的交往,也仿佛按照一年四季的温度发生着变化。
走得最近的季节是夏天。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是个钓鱼狂,就邀请我到南大川来钓鱼,说是还我请他吃牛肉面的情。据他说,自己干活儿的砖厂厂长有一个专门用来钓鱼的鱼塘,放养了五千斤鲤鱼和鲫鱼。他还口气不小地让我把想带的朋友都带来。哈哈,这倒不错,没想到还能凭着曰福的面子不用花钱白钓鱼。
对钓鱼的人来说,再没有比接到钓鱼邀请更令人高兴的事情了。
等等,这会不会也是吹牛呢?我突然产生了怀疑。即使是钱再多的私营企业家,难道就能在鱼塘里放养五千斤鱼?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怀疑只是一闪而过。有地方钓鱼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即使一条鱼也钓不到,或者浪费了鱼钩和鱼线,也是钓鱼的趣味之一。
第二天,我领着一帮钓友来到南大川。尽管甩开鱼竿等候了一个上午,静静的水面上却毫无动静,只有零星的小鸟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
这不明摆着被骗了吗!
一条鱼也没有钓着的钓友们苦笑着正要埋怨我时,曰福拎着几瓶酒和几条枯树叶似的鱿鱼干风风火火地来到钓鱼地方,说是让我们先点点饥。
你不是说有五千斤鱼吗……你是不是又吹牛了?
嗨嗨嗨嗨……不要急嘛,先喝一杯。
曰福一副坦然自若的表情。
看来我相信你实在太愚蠢了。你真是让我在一起来的朋友面前丢尽了脸。
嗨嗨嗨嗨……我说你别着急嘛。
曰福发出其特有的笑声,蹲在我身旁,悄悄地把用米糠、豆面、蚕蛹面等拌好的鱼饵放在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里的鱼专咬这种鱼饵。
是吗……可气味怎么这么难闻?这是什么鱼饵?
我总觉得鱼饵应该有股香味儿,像这种散发出臭豆腐气味的鱼饵令人恶心。
嗨嗨嗨嗨……你就试试看吧。这可是我们厂长偷偷拌制的,我也不太清楚。你知道就行了。
我只好掉换了鱼饵。
哈哈哈……这是怎么回事?
鱼钩刚一放进水里,鱼就上钩了,鱼漂像滑落似的迅速下沉。我连忙拉钩,手上顿时感觉到了鱼儿勇敢挣扎时发出的战栗,鱼竿反弹得十分厉害。这可是真正的钓鱼趣味。
你多钓一些就行了。嗨嗨嗨嗨……这都是厂长花钱放养的鱼,都钓走了能行吗?钓不到鱼是因为没有技术,哪能怪鱼呢。
哈……典型的乡下人的狡黠。能在曰福身上看到这种表面上客客气气、实质上让人下不了台的单纯狡黠,让人感到十分新奇。既然把你们请到钓鱼的地方来,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本事了。曰福这种乡下式的狡黠,既给了我和朋友面子,也给了鱼塘主人面子。
见我接连不断地钓上鱼来,那些大声埋怨鱼塘里没有鱼的朋友们纷纷闭嘴。我偷偷地告诉他们,这里的鱼不咬带有香味儿的鱼饵,喜欢咬带有臭味儿的鱼饵。于是,钓友们也都掉换鱼饵,不一会儿都钓上了几条鱼,原先的遗憾一扫而空。
我也因此挣到了面子。尤其是那天晚上,曰福强把已经打算回家的我们留下,用羊肉和羊杂碎招待,让我们留下了朦朦胧胧的美味记忆。曰福白天没露任何声色,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悄悄地准备好了这桌酒席。事情的确干得漂亮,甚至让人怀疑这竟然是曰福一手办成。只是让曰福年迈的老母亲在锅台旁忙得团团转令人过意不去……除此以外的乡下气氛,让我们这帮感情丰富的记者颇为新鲜。
原以为曰福只是个开口借钱、一口气吞下三碗加州牛肉面的粗人,没想到竟然也有可爱之处。
曰福,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家,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人。
后来,曰福来找我找得更勤了,依然是不讲任何礼节。他就这样跳进了我的生活圈。他既是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家,也是我的朋友。
可如今他要结婚了。
在去钓鱼的路上,我把事情告诉了钓友们。大家都显得一筹莫展,纷纷提议先去南大川把份子凑上后再直接去钓鱼的地方。于是,我们一行人先去了南大川。
当我一见到曰福光秃秃的额头和不合身的西装,一听到嗨嗨嗨的笑声,立即感受到了某种莫名的悲凉。我很快就作出了让钓友们先走的决定。
嗨嗨嗨嗨……你看看,这里哪有能当傧相的人啊。
新娘呢?
正在屋里往脸上涂脂抹粉呢。嗨嗨嗨……是个蒙古族女人。
蒙古族?
没错,嗨嗨嗨。
他要和蒙古族姑娘结婚!
要说是举行婚礼的人家,来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且清一色全是老头老太太。连贪婪于婚礼上糕点的孩子们也没有,无疑就是正在崩塌倾斜的农村的缩影。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曰福不加说明,我一下车就感到今天的钓鱼在这里已经结束的原因。
曰福的婚礼完全无视祖先留下的婚礼惯例,办得极其简陋,加上阴沉沉的天空中沥沥拉拉地下着雨,使得帮忙的人和客人们的情绪更加一塌糊涂。婚礼毫无秩序,就连在新郎家里大致化妆的蒙古族新娘也没穿婚礼上应该穿的婚纱,只是穿着一套很普通的朝鲜族衣裙坐在婚桌后面。
现代婚礼程序中经常能见到的结婚宣誓、证婚人讲话、交换礼物等仪式全部被删掉了。一句朝鲜语也听不懂的蒙古族新娘,木雕泥塑一般默默地坐在那里,似乎对婚桌上煮熟的公鸡嘴里叼着的红辣椒很感兴趣,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新娘黑黑的脸上因经常干重活儿显得疲惫不堪,还留下了花花搭搭的化妆痕迹,人长得又干又瘦,仿佛一阵风就能刮跑。作为一个担负着生儿育女任务的候补母亲来说,体格真是令人担忧。
嗨嗨嗨嗨,今年砖厂从内蒙古新来了许多打工者,其中龙梅被我看中了……曰福坐在婚桌后面,我作为傧相坐在他旁边。他把手搭在我肩上洋洋得意地说起了自己的结婚经历,完全是一副找到了天下第一美人的样子。
我领着龙梅一起去了一趟内蒙古,那里只住着她年迈的老父亲。于是,我干脆就把她老父亲一起接了出来。她家里实在太穷了……连房子也没有,住在又破又旧的帐篷里。蒙古族本来不就是住帐篷过着游牧生活的吗……曰福不可能不知道啊……而且他说“太穷”,很难让人想象出怎么个穷法。
曰福就这样摆脱了光棍生活,并以娶亲的仪式结束了“羽化”过程,摘掉了光棍标签。蒙古族姑娘龙梅则嫁给了比自己整整大15岁,毫不般配的朝鲜族光棍。延边南大川的曰福有了个曾在草原上骑马驰骋的老丈人。人生就是这样无常。
后来,曰福领着龙梅到延吉来过几次。每次来都要吃上三碗加州牛肉面,并当着我的面数落她不讲卫生,不会操持家庭生计。他的妻子连一句朝鲜语也听不懂,只是轮番打量着我和丈夫的脸色,脸上露出窘促难堪的神情,可怜兮兮地坐在那里。曰福自己本来也不是一个讲究干净的男人……看来是出现了生活差异,开始产生冲突了。
据我观察,曰福似乎经常会对龙梅大声吼叫,而龙梅总是低头不语,百依百顺。因此,在两人的生活中仿佛并不存在什么太大摩擦。其实,夫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要互相顺意,不在一起时互相思念,生病时互相用手摸摸额头就够了,不需要只是为贪婪对方容貌才走到一起。一方咄咄逼人的话,另一方甘拜下风;即使互相有什么缺陷也轻轻地一笔带过,这样才会有和谐的夫妻关系。
我总是像个长辈似的指点曰福,应该理解蒙古族与我们的习惯不同,曰福则总是用嗨嗨嗨的笑声来回答我的忠告。我的妻子经常送龙梅一些化妆品和衣服之类的东西,龙梅收到礼物时总是先表示惊讶,而后轻轻一笑。
说实话,他们是一对很有意思的夫妻。每次见到他们,总会让我想起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后来以《牧马人》的题目改编成电影)。他们就是两个现代版的“牧马人”。
自打结婚以后,曰福突如其来的出现和冷不防开口借钱的现象销声匿迹。我原以为他这种陋习已经根绝,谁知却并非如此。
有一天临近下班时,曰福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张口就要借500元钱。据他说,妻子因为临产住进了医院,需要先付2000元,自己还短缺一些钱。他那连续发出嗨嗨嗨的样子不见了踪影,变成了一副极其焦急的模样。这可是生孩子的大事,怎么可能拒绝呢!
“医生说,龙梅生孩子的管道太窄,孩子生不出来。所以,我只好领她到延吉的妇幼医院来做手术……也不知道生个孩子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延吉医院里全都是一些见钱眼开的家伙!”
什么时候生?
我到财务那里临时借了500元钱交给曰福。
大概还有几天时间吧。
曰福拿着钱返回医院,不料第二天又来找我。他说,妻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孩子生下来,而自己无病无灾,与其整天坐在床头流着口水打盹儿,还不如找个合适的打工地方挣些钱。
你要是早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存一些钱的话,至于这样吗?可你总是把挣的钱花个精光,才会遇到如此难处。
谁说不是呢?结婚的确不是好玩的,嗨嗨嗨。
我十分为难,眼下到哪里能找到合适的打工地方呢?
如果去延吉劳务市场的话,找临时打工的人拥挤不堪,而打工的地方却严重短缺……尤其男的更不好找活儿,要是女的还能找到在饭店里干些杂活儿的工作……可是,又不能给为了挣钱让妻子生孩子而绞尽脑汁的曰福泼凉水。难道真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嗨嗨嗨嗨……不管是什么活儿,只要能挣钱就行。你就出面替我找找看吧。我一见到老婆越来越瘦的脸和高高隆起的肚子,总感到十分不安。我在南大川是出了名的大炮王,可对老婆和孩子我怎么能当大炮王呢!以前的事情就算了,虽说已经有些晚,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老婆饿肚子,还要好好把孩子养大。
我大包大揽地让曰福明天再来,然后把他送走。可是,接下来我不得不为到哪里去找临时工、而且还是给五大三粗的男人而深感苦闷。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光会说大话的嘴巴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
不过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行政科的李科长在去社长办公室途中,顺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啊呀,我怎么会把他给忘了呢?
李科长的个头儿长得像篮球运动员那么高,还是我的钓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求他帮忙找个男人能打工的地方,还把事情的原由告诉给他。李科长脸上露出为难表情,说是男的能干活儿的地方早已满了,只有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朴大嫂请病假没来上班。我喜出望外,李科长却有些为难,男的怎么能干清洁工的活儿呢?我很不以为然,眼下正是饿着肚子、双腿发软、奄奄一息的节骨眼,哪还顾得上区分大麦饭还是小米饭呢!
在我死乞白赖地缠磨下,李科长只好无可奈何地答应先试试看。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曰福叫来了。
嗨嗨嗨嗨,太好了。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乡下人到城里来,管它是黏糕还是米糕,只要能挣钱,什么活儿都得干。
曰福回答得很痛快,迫不及待地去见李科长,然后直接拿起扫帚打扫走廊、拿起抹布去擦厕所了。
男人有男人干的活儿,我为什么要干女人们干的活儿呢?大炮性格的曰福完全能说出这种话来。为了对付他,我还在暗地里做好准备,精心挑选了一些将他置于困境的狠话。不料,他这番举动反倒使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过,曰福二话没说就干起活儿来,倒也让我轻松了许多。我原先对他打扫女厕所还有些担心,可是并没有听到什么反应。
如果就停留在这个程度上的话,曰福的临时工作将会静静地开始,静静地结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十分勤快地走遍每个办公室,不但收拾没用的废纸,还热情地把烟灰缸擦拭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他还把办公室里床上的被子拿去洗得干干净净。
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年过四十、谢了顶的大男人,用他那粗糙双手洗被子的场面,让人想起来都会觉得十分壮观。各部门为方便值夜班都准备了床和被褥。原先负责打扫卫生的朴大嫂只管走廊和厕所,对办公室里的一切从不干预。这是行政科规定的界线,所以一直没有任何异议。然而,曰福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道无言戒律,勇敢地踏进了办公室。据行政科李科长说,曰福还自告奋勇地每天晚上值夜班打更。他每月工钱500元,对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少了点。
他是谁?
一开始,每个办公室都冒出这样的问号,但是仅仅几天时间,问号就变成了感叹号。听说是崔老师的亲家……我和曰福的关系暴露无遗。一般来说,记者们经常使用老师的称呼,但是对这个从乡下来的男人,而且还是个经常连续发出嗨嗨嗨笑声的谢顶男人,显然不能用老师相称,只好含含糊糊地叫一声“亲家”。霎时间,曰福在记者们中间被通称为“亲家”。这个为人幽默的“亲家”顿时成了新闻人物。
我们办公室里的被褥也毫无例外地成为曰福手中的猎物,第二天才重新物归原主,就像女人们洗的衣物那样,散发出刚洗过的清香,闻了颇感舒服。就连在走廊里遇见总编时,总编也称赞说:听说新来的清洁工是你的亲家,干得不错嘛。
只花了几天时间,曰福就成功地让人们一般都会遗忘忽视的清洁工地位浮出水面。
行政科李科长最初看上去很不满意,现在却亲自跑来满脸堆笑地对我说,看来朴大嫂不可能再回来干活儿了,同时还表达了想与曰福签订长期用工合同的意思。不过,这好像不大可能。因为曰福住在乡下南大川,而不是住在对农民工只会榨取不懂爱护的延吉。
就在曰福做了二十几天清洁工以后,他的妻子接受了剖腹产手术。这对于曰福来说,无疑是最最高兴的事情。因为孩子在龙梅腹中一直没有想出来的意思,因此他总是怀着一丝淡淡的忧虑。
我让妻子煮了一些海带汤,然后一起赶到妇幼医院。时间已是夜幕降临的夜晚了。
延吉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妇幼医院是孕妇们聚集、孕育新生命的地方。与别的医院不同,这里充满了生气。刚走进医院走廊,就能听到不时传来的婴儿啼哭声。说实话,世上再没有声音比新生命的啼哭更加动听了。这声音伴送我和妻子走进龙梅所在的病房。
啊呀,双胞胎!
刚走进病房,妻子就发出了惊喜的欢呼声。女人的眼睛就是不一样。
什么双胞胎?电话里没提起过呀……再仔细一看,的确是双胞胎。哈哈,曰福本事不小啊。
嗨嗨嗨嗨……我也没想到。
曰福这次嗨嗨嗨嗨的笑声,听上去比任何一次嗨嗨嗨都更加明朗。
是辣椒还是菊花?
一个辣椒,一朵菊花。嗨嗨嗨嗨,龙凤胎。
嗨,这真是南瓜藤上结西瓜,喜上加喜啊。
龙凤胎是老天爷的恩赐啊。
妻子直到今天还想再生个孩子,因此难以掩饰发自内心的羡慕。
龙梅刚做完手术,尚未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听到我们的声音后,她慢慢睁开眼睛,轻轻点了点头,然后没有丝毫羞涩地敞开并不丰满的胸脯给双胞胎兄妹喂奶。曰福在一旁怜悯地看着妻子,轻轻地抚摸着妻子被汗水打湿的黄头发。完全是一副感人的戏剧场面。
你能不能再另外给我找个打工的地方?龙梅手术时流了很多血,医生让在医院里多住些日子……
我们那里的活儿怎么办?还想与你签订长期用工合同呢。
那里的活儿早晨、晚上半天就能干完,白天就没活儿可干了。
你是不是太贪心了?
嗨嗨嗨,我干起活儿来从来不知道累。
我再给你打听打听。
我头一次没有丝毫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妻子把装有钱的信封塞在龙梅被子底下,说是给孩子买些牛奶。
太谢谢你们了。我不管干什么活儿,也绝不会让为了我来到这个世上的双胞胎兄妹挨饿的……我还要好好保护对我无限信任的龙梅……
话没说完,曰福突然停下来转过头去,眼泪成串地滚落下来。
曰福哭了?曰福竟然哭了……
我是不是太笨了?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会流眼泪……
在华丽的路灯闪耀中,延吉的夜晚正在静静地浓郁起来。
曰福与龙梅……以及难产的双胞胎……而且是蒙古族母亲和朝鲜族父亲孕育的双胞胎……希望这座城市可以给孕育了这对双胞胎的曰福和龙梅多些宽怀和爱心吧……
(译自《延边文学》200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郭金达
刊于《民族文学》2011年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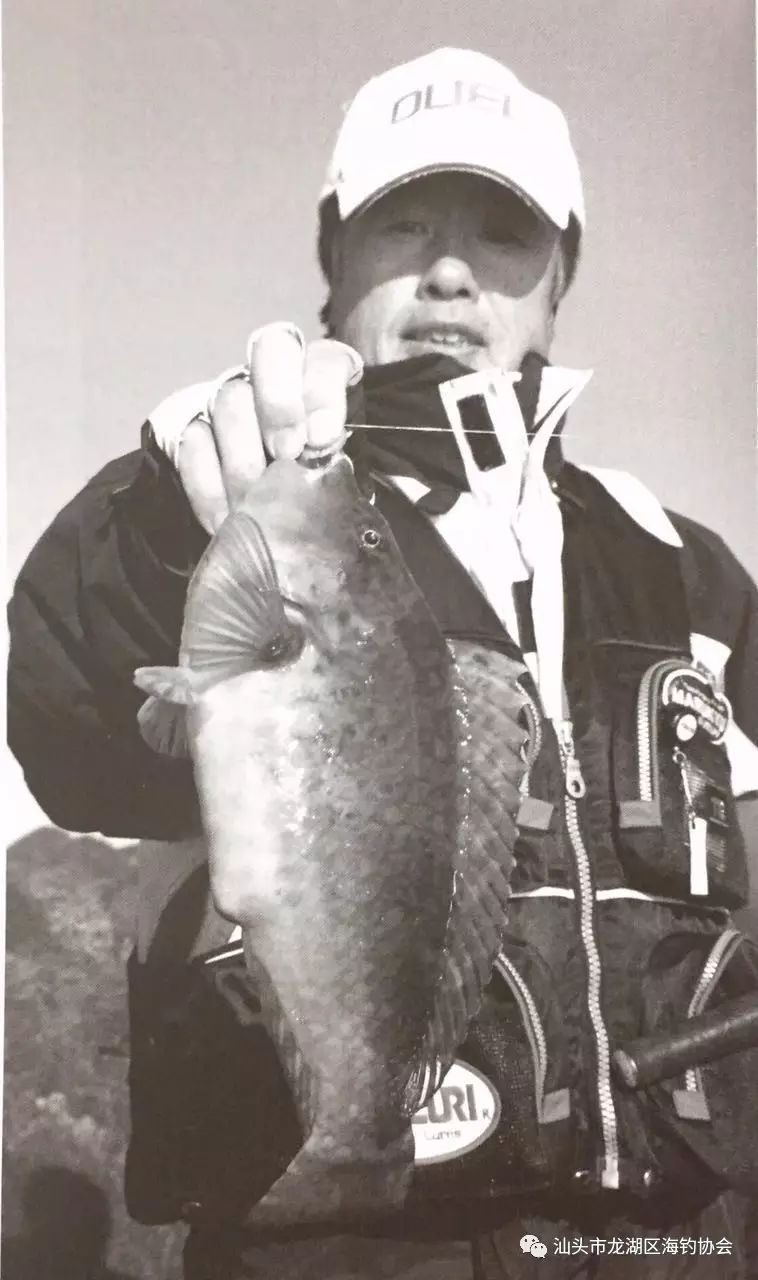


![[钓鱼知识]两招轻松提高鱼的上钩率](http://img.diaoyuma.com/?url=http://mmbiz.qpic.cn/mmbiz/PLnKAVdOXicJPfNkIcmYdK4z2L051xo7SxED53cxm6XlUWYYjLkrG2Oc3duZsyibRUt5v1umSMWibBDleO1CRwBGg/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