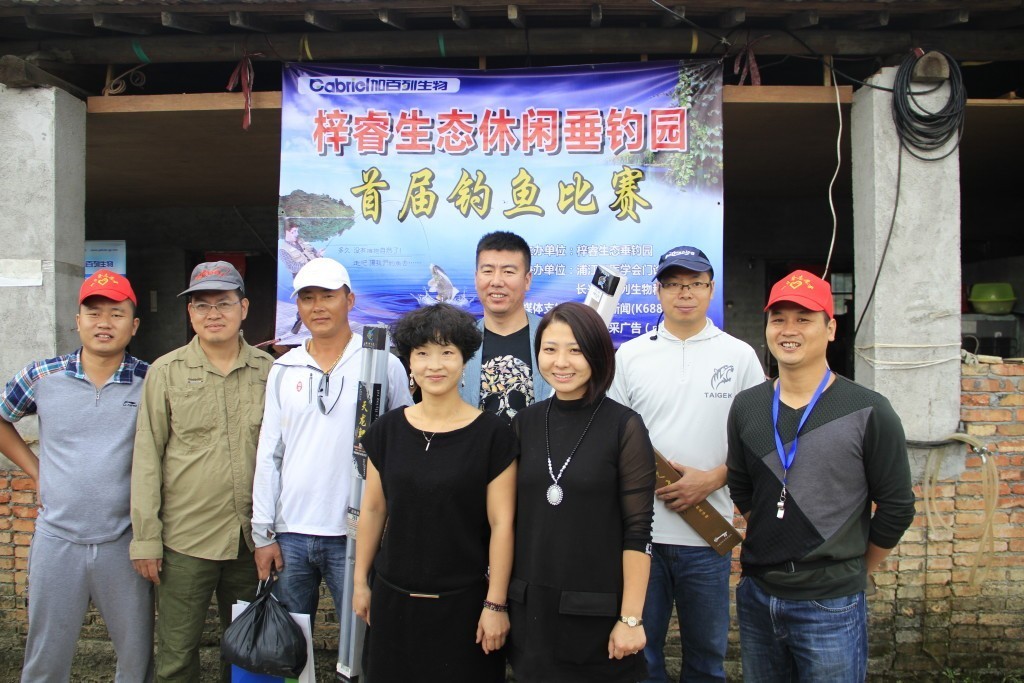“小姑娘你知道吗,人死后会去到哪里?”
她拥抱了我一下,告诉我:
“我觉得,人死了之后,会住到爱你的人的心里。”

大智若鱼
by 猫力

1
去英国之前, 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与憧憬。我总觉得去发达国家旅行会比较无趣,那里的生活节奏很快,城市生活压力巨大,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精准的关系,我担心当地人不会有很多的闲暇与我们这些游客聊天,再加上英国素来给我一种严谨古板的印象,所以,我基本上只带着看一看大本钟和福尔摩斯的最低期望。到了英国之后,我特意找了一个郊区的房子住下,一来希望远离市中心,二来也是想让自己这个大闲人玩得更自在些。
我的房东潘妮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和自己的三个小孩儿—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和我遇到过的许多民宿主人一样,潘妮也是一个风格独特的艺术家, 她平时都忙着摄影、拍电影、绘画, 有时候也会突发奇想做一些艺术装置。她长得并不那么像我想象中的英国人—合体的素色套装、考究的丝巾和手帕、分寸感极强的举止和一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不好意思,我一定是《唐顿庄园》看多了……我的房东扎着一头脏辫 给人一种粗犷、野性的感觉,说起话来表情丰富,我想她出现在佩姆伯顿的《疯城记》(Psychoville )里,也一定毫无违和感。不过,因为一开始潘妮并没有主动地与我热情交流,而且她总是很忙,我还是有点怕她,怕打扰她的工作,不敢和她说太多的话。
潘妮的房子是奶奶留给她后自己改造的,淡绿色的墙纸,上面缀满了许多画作,有些地方也会挂一把提琴或者一些形色各异的壁灯。从客厅到各个小房间,到处都有颜色各不相同的木质家具,电视柜、衣帽架、无数的小台面等。但最让人觉得惊艳的是房子里无处不在的小门,每一扇都留着时间的痕迹。远看时,我以为这些都只是仿古做旧的效果,但当双手触及它们的表面,就能感觉到那些木块浑然天成的肌理与包浆。
我觉得诧异,就问她这些门是从哪里弄来的。
她笑笑说,自己也非常喜欢旅行,这些门是她在摩洛哥发现的—她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树枝、树干、木块。在摩洛哥,她可以忍住不花一分钱购买当地的华美首饰和漂亮衣物,但唯独这些门,她会倾尽所有去购买和交换。
有一次, 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 身边有一个形状怪异的单门柜, 上面的门非常独特。我的眼神瞟过那扇门时, 她努了努嘴, 示意要说这扇门的故事了。
有一次旅行,她来到摩洛哥一个小村落,当地人基本都以牧羊为业。傍晚时分,她走过一栋房子,准备向那户人家求宿时,发现了一个别致的羊圈,她一眼就相中了这个羊圈上的门。于是,她立刻摘下自己腕上的手表和脖子上的项链,要求以物换门。就这样,她拆下了那扇小门,一路扛回了英国。
回来之后,她就开始想怎么安放这扇门,一番思索后,又找来几块别的木材,加工打磨,于是有了现在这个单门柜。同样,房间里其他每一个自制木家具背后也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比如她的衣帽架。有一年,她在马达加斯加旅行时,在路边看到一根很粗的树枝,上面还有几根零星的细枝,她觉得这一截长短适宜,样貌也好,就背了回来,立在客厅,成了一个衣帽架。为了防蛀虫,她将它漆成了米白色—每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像是一个年迈且热心的侍者,欢迎每一位到访的客人,并帮他们脱下外衣,安置妥当。
她自己住的顶楼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露台上摆着一个很大的木桶,边上有一段水管和一个莲蓬头。天热的时候,她每天都会赤身裸体地在露台上洗澡,还开玩笑说,家附近就是机场,说不定有很多飞行员早早就暗恋上了她,并且每次飞机起飞、降落时都会偷窥她呢!
2
聊完这些故事,我和潘妮也熟了起来。有一天早上,我特意早起,想为慷慨善良的房东煎个鸡蛋当早餐。但是我没看见煎鸡蛋的铲子,于是在厨房到处找。突然,我在微波炉后面翻出一张老照片,黑白的,上面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手里拎着一条跟她差不多高的鱼。照片画面非常吸引人,我就找来潘妮问她:
“这是电影里的画面还是杂志上的剪报?”
她听到后微微一笑,说:“这是我的母亲。”
我先是一惊,然后又立刻追问:“这条鱼是真的么?”
她笑得更大声了:“哈哈哈哈哈,我母亲是一个fishwoman,是一个我很敬佩的女人。”
“那你介意跟我说下她的故事吗?”我又问。
“今天是英国的母亲节,我刚好下午要去郊外见她,开车大概三个小时,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她说。
“没问题!”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
于是我买了一些花儿,她开着车,载着孩子。一路上,她简单地跟我说了她妈妈的故事。
在她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她妈妈四十五岁时,她的爸爸就去世了。她爸爸是一个警察,在调查一个犯罪案件时不幸身亡。在那之前,潘妮一家六口人过着十分幸福安逸的生活。爸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英国男人,他养了一只猫头鹰,还经常带着这只猫头鹰去河边钓鱼。可是这一切都随着爸爸的去世消失无踪了,甚至因为爸爸去世得太突然,潘妮的妈妈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们相恋了三十多年,青梅竹马,感情一直是那么稳固悠长,从未想过要以这样的方式阴阳两隔。她妈妈常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一个毫无天赋的普通女人,唯一的天赋就是能让她的爸爸爱上她,并且心满意足地做她的好丈夫。对她而言,丈夫的过世就如整个世界崩塌一般。她每天以泪洗面,反而是自己的孩子们更早地接受了现实,然后去安慰她。
每当想念丈夫的时候,潘妮的妈妈都会去丈夫以前常常钓鱼的那条河走走看看,有时偶尔也会带上丈夫生前留下的渔具去那边钓鱼。但她其实一点儿都不会,只是做着与丈夫相同的事,幻想着这一刻,他们彼此的联系并未因生死而切断。
有那么一天, 刚好是她丈夫去世一周年的日子, 她又在河边钓鱼。她一边想着丈夫, 一边流泪。附近有一些职业的钓鱼客路过, 就在一边取笑她:“ 看那边那个中年妇女, 钓鱼的样子又蠢又笨……”
那些职业钓鱼客一致认为, 在那个季节, 在那种水流情况下,那片水域是绝对不可能钓得到鱼的, 就算有鱼, 看她的样子, 也不可能把鱼拉上来。他们越说越起劲儿,甚至专门停下来观赏这出喜剧,嘴里的言辞也越来越刻薄。
“What a silly woman!”
“Haha, stupid woman!”
……诸如此类。
但是潘妮的妈妈并没有理会,她一心只想着她的丈夫,心中凄然,眼眶湿润。而职业钓鱼客们还是不依不饶。
可就在这时候,她突然感到手中的鱼竿有了强烈的震颤,她大叫:
“Help! Help!”
有什么东西正在拽她的钩子!
旁边的职业钓鱼客就跑过去帮她,帮她钓起了那张黑白照片上的鱼,大概有一米五长。
那条鱼是那个小镇上迄今钓到的最大的鱼。所有人都非常惊讶,谁都不会想到一个毫无经验和技巧可言的家庭主妇竟然钓上了这样的大鱼。这件事立刻轰动了当地,人们口口相传。很快,这件事就成了当地的新闻,并上了报纸,于是留下了我在厨房看到的那张照片。而潘妮的妈妈,也正是因为这条鱼,开启了她将近五十年的钓鱼生涯。

潘妮一路上都笑着跟我说这个故事,而我听到“五十年”一词时,立刻就惊呆了。
“什么?五十年,你妈妈现在还在钓鱼吗?”我问。
“是的,她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她上周刚从非洲回来,而且因为钓的鱼太大,用力时断了一根肋骨,休息了两个星期,现在已经好多了。不过她又订好了去荷兰的机票,马上又要去那边钓鱼了。”她说。
听完潘妮说的故事, 我几乎瞬间忘记了自己是在英国,行前那些可笑的偏见也都随风而去了。我们根本无法低估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你不知道在同一片星空下,与你出身、教育、经历完全不同的人们究竟在做着什么梦。我想象着在社会新闻中才会出现的九十二岁老人的样子,有一天只身背着渔具出现在荷兰机场,她意气风发,像一个从未老去的女战士,而她的过往犹如一首动人的抒情诗。那真是一个令人沉醉的下午,我一路吹着风,期待见到那位传奇的老奶奶。
3
抵达郊外的一处民宅,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女超人”。她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顶多六十多岁。她一头金发,衣着考究,说话时中气十足,可以想象她身体还是非常的棒。
见了我之后,了解到我是从中国来的旅客,并且对她钓鱼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她也就热情地跟我讲起其中一些难忘的经历。她向我展示房间里的一张钓鱼地图,是用白纸手绘的,并不特别精细,但形状也能大概标示各个国家了。地图上面画着许多小红点,密密麻麻,表明这些地方是她去过并钓到过鱼的。四十多年来,她去过蒙古,在蒙古包里住了好几个月;去过俄罗斯,当时俄罗斯有一个军官非常欣赏她,于是开着军用直升飞机,带她去一块未开发的内陆河,让她在直升机上往下钓鱼;她也去过印度,她打听到,当地的鱼非常喜欢猴子屎的味道,于是特地先去山里收集了很多猴子屎,用作鱼饵。她每年都会写一本钓鱼日记,收纳箱里已经有了好几十本。从荷兰回来后,她准备休息一阵,然后将这些日记整理出来,写成一本传记。她说这本传记不求出版,但希望能把自己这一生忠实地记录下来。
她说她这一生是从自己四十五岁那一年才开始的。钓鱼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天赋,别人钓不起来的鱼,她都能钓到—而且那些鱼不是特别大,就是品种特别奇特。少数时候,她也会跟这些鱼合个影,但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亲吻那条鱼,然后放它走—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Kiss the fish and let it go。
她用的kiss 这个词顿时让我脑中浮现了一个童话般的画面,如果潘妮是《疯城记》(Psychoville )里面的角色,那老奶奶一定是蒂姆·波顿的电影《大鱼》(Big Fish )里的人物了。就像《大鱼》里的父亲,一直生活在奇幻的故事里,死的时候也要回到故事里去。我问她:
“你有没有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丈夫与你重逢的另一种方式?”
她笑了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说: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
她给我看他丈夫去世前一年照的全家福。她很甜蜜地依偎在丈夫身边,他手里拿着一个网球拍,头上顶着家里养的猫头鹰。四个小孩围坐在身边。一个很幸福的画面。
我突然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她丈夫用另一种方式在为这个家庭担负责任—即便他已经不在现世。他希望自己深爱的妻子能找到另一种活着的方式,同时,这也一定是他在冥冥之中,用这种方式给了她一种坚持活下去的动力,并且一次次地与她重逢, 跟她亲吻, 跟她say goodbye,让她在后半生更加懂得“放下”—放下她已经钓到的鱼儿,放下他死去的事实。
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出门。我关门,和老奶奶说再见。这时,她问我:
“小姑娘你知道吗,人死后会去到哪里?”
“我不知道。”我说。
她拥抱了我一下,告诉我:
“我觉得,人死了之后,会住到爱你的人的心里。”

4
回程的车上,潘妮一路吹着口哨,而我还沉浸在她妈妈的故事里。我想:若他是鱼,那她一定是让他可以安静躺下,缓缓流动的水。这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假,只需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事情就好。这时潘妮突然在一个转角的路口停下,夕阳刚好透过车前玻璃洒到她那一头凌乱的脏辫上,她转头,歪嘴笑着对我说:
“其实潘妮是我的昵称,以后你可以叫我的本名,潘多拉。”